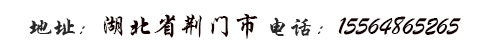冈仁波齐峰下的唐卡画师告诉你什么是信仰和
|
白癜风容易康复吗 https://m-mip.39.net/nk/mipso_4639147.html 在尼泊尔靠西藏版图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圣山冈仁波齐峰注视下,是高原上远离人烟的多尔普(Dolpo)地区,由于地势远,海拔高,没有电,没有路,半农半牧,被众多冒险家说成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村落,雪山和高原以及与文明相隔甚远的地位置保存了其藏族纯粹的传统文化。 一百多年前,还未被徒步者发现之前,只有那些去转山的朝圣者才会从这里经过。丹增洛布喇嘛(TenzinNorbuLama)的家族祖先,举家开始了前往冈仁波齐峰朝圣者的旅程。路途遥远,全家老小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雪山宏伟,人畜渺小,在数年的转山的过程中,由于恶劣的天气和气候,丹增洛布喇嘛的远亲,年迈的领头人没有熬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高原气候,去世了。仿佛是雪山的启示,整个家族在附近多尔普地方一处村庄扎根,新的生活开始了。 对祖灵的想象,对多尔普地区的记忆,那些亦神亦人的神话和历史,成了丹增洛布喇嘛画作中的场景,与传统唐卡不同的是,在他的画布里,村民收割麦田,赶着牦牛翻越雪山,隐士端坐山间,巫师在门前做法治病,山顶天葬师傅分割尸体,云端上的佛祖遥望着众生。 平凡的生活,永恒的一天“没有什么比平凡的生活更伟大了。”年过四十的丹增洛布喇嘛,赤脚身着牛仔裤衬衣,在巴黎老友艾瑞克?瓦利(Ericvalli)家的沙发上盘腿而坐,从他第一次走出尼泊尔藏族山区的寺庙已经二十多年了,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寺庙生活,从来没有见过电灯,没有喝过可乐,甚至没有见过一棵树。而如今他的画展在纽约、东京、巴黎、苏黎世等世界各地的画廊博物馆展览,在世界来来回回一大圈。但每年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徒步一周走回大山中,回到当初他长大的村庄,穿着牦牛皮做的藏袍,没有电的夜晚,在篝火点亮的夜里喝一碗酥油茶。 藏语里把唐卡画师统称为“拉日巴”,意思是画神佛的人,他们手中都有一份世代相传的规则,必须遵循。唐卡严格按照《造像度量经》的标准绘制,似乎千人一面,而各有不同,其中规则往往隐匿于密存的经典中,记载着至少八种成套的造像尺度,无论是姿态庄严的静相神佛,还是神情威猛的怒相金刚,所有的造像都有相应的比例,为了保证形象不会走形,并易于辨认,利于宗教教义的传播,不得修改。 游牧为生的藏民在辽阔而荒凉的高地上逐水草而居,裹成一卷的唐卡成为随身携带的庙宇。唐卡画师用粗疏的麻布涂抹天地,用一笔一画制造着移动的佛龛。唐卡系挂的地方,就能成为一种象征,让虔诚的信徒祈祷、礼拜、观想。最小的唐卡仅有巴掌般大小,画在纸上、布上或羊皮上;而大的唐卡可达几十甚至上百平方米,每年择吉日而向广大信众示现,缓缓展开后遮住整整一面山墙。
藏人祖灵沿着喜马拉雅山的血脉与脊梁携家带眷,那至高的行装是一卷卷精致而神圣的唐卡。从形式上说,唐卡,既是一种卷轴画,这种形式在中原也流行,其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便于携带;从内容上讲,唐卡的精神内核并不仅仅局限于寺庙之内,只是佛教在西藏兴起之后,除了供信众朝拜、观想,它更是传播宗教精神的祥云。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样的绘画风格根本来自哪里,如果追溯遥远的时代,会发现那些原始的人类共性幻化成了不同的绘画风格又在四处交融汇合,相映成趣。唐卡所保持的严谨风骨至今犹存的最大秘密可能恰恰在于其“因循守旧”,“守旧”在此象征着唐卡的光荣传统,每一位画师正是因为坚守这一传统而成为文化记忆的复制者。 由于世代都家族都是唐卡画师的缘故,丹增洛布喇嘛在多尔普地区最古老的寺庙长大,8岁开始学习经文和绘画。年轻的丹增洛布喇嘛一直遵循世代相传的规则范本,虔诚地按照传承千年的规则作画,业精于勤,在寺庙里的20年,每日四点起床打坐,研制颜料,打磨画布,20岁他已经成为小镇里赫赫有名的“拉日巴”。这20年间,他从未走出过寺庙,也没有想过外面的世界。“那时日子如窗外的太阳,按时起起落落,规则被先人写在宝典上,当时从来没想过外面的世界,更不知情,如果艾瑞克?瓦利没有来,我会像这样这样规规矩矩地过下去吧。”看着自己二十多年前在寺庙里作画的照片,丹增洛布喇嘛摸摸头,感叹道。 年,国家地理摄影师,奥斯卡提名电影《喜马拉雅》导演艾瑞克?瓦利来到多尔普,在领头人告诉了他丹增洛布喇嘛的名字后,一路按图索骥去寻找这位年轻的唐卡画师。年代久远的寺庙木门被推开,里面装着的,是香火的烟气,时间的尘土,19岁的丹增洛布喇嘛正坐在角落里专注地起稿,艾瑞克.瓦利按下快门,留住了经典的一幕。 “我从来没有出过寺庙,更没有见过黄毛蓝眼的外国人,当时艾瑞克像外星来客,推开了外面世界的大门。” “洛布,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艾瑞克那时问他,“除了描绘佛像,你愿意去画你的村落,你的人民吗?与其画万古的佛像神灵,不如画在你眼前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吧。”“我被这个疯狂的想法吓到了,‘外面’、‘旅行’这些字眼是我生命中没有出现过的。”丹增洛布喇嘛有些犹豫,他希望生活保持其淳朴的模样,就如同画面上的神佛,因循守旧。他拒绝了艾瑞克的提议。 艾瑞克并没有就此放弃。第二次再来村庄的时候,他给洛布带去了画笔和原浆画纸。丹增洛布喇嘛不安地跑去问父亲。“这个外国人要干什么?”父亲问。“他让我走出寺庙,和他四处旅行,学画画,画我亲眼所见的藏民生活。”年纪轻轻的丹增洛布喇嘛思索了半天,老实答道。“这个人带你四处旅行去看世界,还教你画画,还白吃白喝,你为什么不去?”父亲淳朴的反问点醒了少年。窗外,年迈的师傅告诉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出去吧”,父亲又劝道。他收拾好了行李,告别了师傅,看了看自己长大的院子,推开门,从此走出寺庙。 外面的世界丹增洛布喇嘛还无法和艾瑞克沟通,他只会说藏语,而艾瑞克说尼泊尔语。“一开始很难,洛布很害羞很紧张,因为语言不通,我们很难沟通,但随着旅程的进行,我们开始逐渐了解对方”,两个多年好友围坐在客厅篝火边,一起回忆起久远的旅行。如今,洛布不仅会讲尼泊尔语、英语,也会说法语。 丹增洛布喇嘛是苯教徒,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苯教是藏区的本土宗教,漫长久远的苯教思想,是包罗万象的藏族文化根源。在这个高山环绕的偏僻山区,藏族文化中的苯教传统被喜马拉雅山脉尚好封存了起来,这里的人民的生活习俗如千年前一样。 艾瑞克给洛布带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bosch)和老彼得?布吕赫尔(PieterBruegeldeOude)的画册。博斯和老彼得是文艺复兴时期前后惊为天作的大师,博斯擅长画宗教传说,民间神话,却与一般的宗教画家完全不同,他用故事中的象征符号,魔鬼,半人半兽给传统神话新的寓意,画面晦涩难懂,多在描绘人类道德沉沦的罪恶,被视为超自然主义启蒙者。而老彼得是以描绘中世纪欧洲自然,生活景象为名,他深受博斯画风影响,在西方社会,他是第一批以个人需要而作画的风景画家,跳脱过去艺术沦为宗教寓言故事背景的窠臼。 两个人一页一页翻看画册,15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是画家从教堂走入生活的时期,20年前的丹增洛布喇嘛同百年前与他们有一样的疑问,是继续描绘神像,还是描绘生活。艾瑞克和洛布没有说话,静静地翻看画册。洛布抚摸着其中一张《冬季捕鸟陷阱风景》,那是一张描写中世纪冬日村民打猎的情景的画作。“好美”,洛布用简单的尼泊尔语说。“可是,现在的欧洲,这样的生活都消失了”,艾瑞克一字一句的告诉洛布,“我们只有看这些画册,怀念我们逝去的生活”。 新世界的旅行还在继续,丹增洛布喇嘛开始逐渐明白艾瑞克看待他文化、宗教、艺术的方式。他跟随艾瑞克的全家,妻子和两个分别5岁2岁的女儿在附近山区附近的部落村寨旅行。几年之后,洛布终于可以和艾瑞克(Eric)顺畅交流。他们一起探访了众多隐匿的山区部落,拜访了悬崖边采野蜂蜜的师傅。在听到了悬崖间采蜂蜜的绝活即将消失的故事以后,洛布对艾瑞克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做了,我的文化,我的雪山,在外面世界的热浪里在逐渐消融,记录这份传统,就是保存这份文化的方式。” 洛布随身的速写本记录着他在途中所看见的景象:运货的牦牛商队,金黄色的麦田上年迈的收割者,骑马扎营的商旅队伍……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们已像家人一样亲切了。艾瑞克问洛布,要不要和他的家人一起回加德满都生活。这样他们可以利用城市的便利安心画画,不必担心有没有柴火和粮食。洛布没有像上次那样犹豫,这趟旅程让他明白许多,他爽快地答应了。 “你们当时怎么旅行的?”我问丹增洛布喇嘛,他憨厚地笑笑,看看我,指了指自己的脚。艾瑞克大笑一声,“走路啊,被惯坏的孩子,你以为是坐飞机吗”,“那你两个两岁、五岁的女儿呢?”我惊讶地问道,丹增洛布喇嘛笑看着满脸不解的我,替艾瑞克回答道,“我们走路旅行了很多年,最后一起走了一个月回到加德满都。以前他带着他的孩子走,如今我带我的孩子走。在没有路的时候,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如今的尼泊尔公共交通覆盖全国,但丹增洛布喇嘛居住的地区依然因为穷乡僻壤,走路到最近的公路至少需要五天的时间。 当年第一次离开,在去加德满都的路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雪山以后。丹增洛布喇嘛突然大叫起来,“树!”,他先用藏语喊,“快看,树!”,他激动地跑过去,摸着树干。艾瑞克此刻才意识到,在高原上的多尔普由于地势险要没有树木可以生存,这还是二十多年来,洛布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树。除了树,还有巧克力,可乐,公路……一个个和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东西,随着距离加德满都越来越近,一次次震惊着少年丹增洛布喇嘛。“没有人赶牦牛了,也没有人用篝火和蜡烛照明,我想起艾瑞克给我看的那些画册,我们的传统和我的旅行一样,伴随着文明的到来,到达了终点。”丹增洛布喇嘛叹了口气说道。 关于藏人绘画的起源,曾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放羊娃,有一天在牧场上睡着了,在梦中看见一位很美的少女,但她很快就从视线中消失了。放羊娃回到帐篷里,为了重现少女的样子,靠着依稀的回忆在大石头上用木炭把她画了出来。人们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是“日姆”,即大山的女儿,后来这个词成了绘画的代名词。尽管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简洁明了地说明了绘画作为一种古老的行为,它的产生与人类的生活、梦境、精神的密切关系。所以,丹增洛布喇嘛的绘画与他关于家乡的记忆、他所经历的变幻万千的生活息息相关。 踏出第一步之后,他看到了寺庙的窗户看不到的风景。“如果没有亲眼所见,很难明白传统的珍贵”他将他的传统习俗细致地描绘在唐卡上,每一处细节,都是他对这个最古老的藏族村落的血脉记忆:用山石与树枝搭起的屋檐、妇女为了节日扎起的发辫、翻越雪原的牦牛群……同时,这些画作中又透露出一个人对现代社会的思辨、探索,传统与新兴之间的纠葛,平和地站在同一张画布上。他的画作与艾瑞克的摄影作品一起,以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视角,呈现出这个藏族村落的珍贵的传统画卷。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采访进行到第二天早晨,我和丹增洛布喇嘛都借宿在艾瑞克巴黎的家里。他这次来巴黎,是为了八月瑞士的展览,顺便来拜访艾瑞克,从他走出寺庙的那天起,二十多年转瞬即逝。偌大的别墅,楼上即有数间空房,丹增洛布喇嘛执意睡在沙发上,“习惯了土床,安稳”。 在加德满都之后的丹增洛布喇嘛,人生轨迹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他的作品一开始是在首都加德满都展出,而后被邀请至美国约翰逊艺术博物馆教学生唐卡,随后在东京、巴黎、苏黎世、摩洛哥世界各地著名博物馆画廊进行个展,作品被许多博物馆永久保存。“你觉得当初你在寺庙里碰见的诺布,和如今满世界做展览的洛布有什么变化吗?”我问艾瑞克,“他还是那个我当初遇见的喇嘛,也许没有从前那样害羞,但是多年的藏族村寨生活让他知道他是谁,也许这就是他如此特别的原因。” 千年前摩西受耶和华之命,率领被奴役的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前往一块富饶的应许之地。佛陀释迦摩尼年轻时离家外出巡游,访遍名师,菩提树下禅定。他们在迁徙的旅途中找到世界新格局,找到自己的天命。 在多尔普地区,没有完全出家的喇嘛,由于地理环境限制生活极其艰苦,年轻人又少,每个喇嘛除了念经,必须耕耘劳作,照顾家人。这也许是洛布为什么天性淳朴的原因,带着宗教的神性,又紧接地气,成功与名望并没有让他迷失自己的位置,反而让他更加清醒。荣格说,那些向外看的人都在做梦,那些向内看的人终将觉醒。丹增洛布喇嘛向外走了一圈,又回到内在的醒悟中去。每年,他都要带着家人回来那个至今距离文明五天徒步距离的村庄,他半年的时间,仍然住在寺庙里。 如今的丹增洛布喇嘛在村寨里建起了学校,也带领无国界医生定期驻扎。远离人烟的村落也有远离文明的缺憾——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因为离西藏很近,一些牦牛商队会在路上捡到一些文明世界用品,像是可乐、糖果、报纸,但没有人知道应该拿他们做什么。”丹增洛布喇嘛说,“村庄里时钟还停在千年前,可外面的世界早就日新月异,这未必不让人担心。” 可是丹增洛布喇嘛也有他自己的迷惑,他想要尽最大可能保护传统文化,也希望村民的生活健康,思想不被封闭的山村所禁锢。但至今,他也没有想明白要不要通电,不通电,山下的灌木和干草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而通电以后,他担心画中的传统宁静的生活会不会也逐渐绝迹。“在多年的旅行里,我不断反省自己做的事,反省我的宗教和人们的生活。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烦恼,为什么我的村落的人就不会。为什么生老病死村民觉得是听天由命,为什么在现代的世界都可以掌握。一个人如何保存自己的本真,不被外界所改变。我们又要如何信仰宗教,信仰生活,如何安心,快乐。丹增洛布喇嘛不知是在问我,还是问自己。在他最近未发表的新画里,丹增洛布喇嘛又朝着革新垮了一步,抽象的画面中,人们开着汽车,大笑着追逐苍蝇,唐卡传统画法与夸张的画面对比下浮动着的,是丹增洛布喇嘛的困惑。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清晨,坐在沙发上刚刚打完坐的丹增洛布喇嘛闭着双眼对我说,“我画的画与我的生活都是一个道理,让我明白,这就是我来的地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baojieshaobj.com/wltq/7597.html
- 上一篇文章: 锦绣bull育儿10项研究告诉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