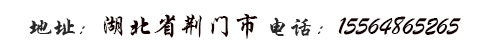真大师还是伪大师
|
真大师还是伪大师? ——重新审视我曾经的偶像里卡多·穆蒂(文 左驰) 意大利,这个南欧地中海的半岛国家,虽然伴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早已暗淡了自身往昔的璀璨光芒;特别是在政治话语权和经济影响力这两个关键领域上,完全是今非昔比,与凯撒大帝在位时风光无限的古罗马帝国之过往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如何破碎与凋零,意大利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大有建树,自始至终都引领着世界文明的主潮流。历经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后,在文艺复兴初期所出现的意大利文学巨匠但丁、薄伽丘到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所涌现出的不朽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再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时期所诞生出的伟大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吉奥吉诺·罗西尼和贾科莫·普契尼等人。亚平宁半岛的文化夜空永远都是那么星光熠熠、灿烂辉煌……意大利积淀深厚的美声唱法(BelCanto)与歌剧(Opera)传统,造就了董尼采第、贝里尼、马斯卡尼、莱昂卡瓦洛等一大批优秀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与此同时,也助推了一代又一代蜚声国际的意大利指挥家。自阿图尔·托斯卡尼尼以降,从老一辈的圭多·坎泰利、图里奥·塞拉芬、维克多·德·萨巴塔、卡洛·玛利亚·朱里尼到后来的克劳迪奥·阿巴多、里卡多·穆蒂、朱塞佩·西诺波利,再到现在中生代的里卡多·夏伊、安东尼奥·帕帕诺、丹尼尔·加蒂、吉奥达诺·诺塞达和法比奥·路易西。意大利这个南欧小国为西方古典音乐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在各自往后的职业生涯里都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且备受推崇的指挥人才。纵然,诸如阿巴多、帕帕诺和路易西都毅然决然选择分别去到德国、英国和奥地利学习指挥,而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由意大利本土所孕育和培养出的指挥家。但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便是他们其中的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意大利歌剧的积极代言人与精彩诠释者。众所周知,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是意大利歌剧的“麦加圣地”,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歌剧演出的最高殿堂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斯卡拉歌剧院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面向公众,为刚刚逝世的意大利指挥家举办追悼音乐会的隆重纪念仪式,这是斯卡拉对曾在这座歌剧院艺术总监职位上有过任期,同时也是最为优秀的意大利籍指挥家最高级别的致敬。而得以享受到斯卡拉歌剧院这一最高礼遇的意大利指挥家则先后被归属于托斯卡尼尼、朱里尼与阿巴多三人。殊不知,还有一位和阿巴多同时代的意大利指挥家与之并驾齐驱,共同构筑起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几十年时间里意大利指挥艺术的闪耀荣光。这个人就是在意大利土生土长的指挥家,那不勒斯人里卡多·穆蒂(RiccardoMuti)。1.穆蒂其人穆蒂年7月28日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父亲是莫尔费塔的一名医生兼业余歌手,而他作为那不勒斯人的母亲,则是一位相当专业的歌唱家。童年在莫尔费塔度过的穆蒂,其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很早就被发掘;8岁时的他开始学习小提琴,后来进一步转向学习钢琴,少年时代的穆蒂就开始入读那不勒斯音乐学院。一次偶然的机会,18岁的穆蒂发现了自己与指挥的缘分,于是乎经常在音乐学院的乐队担任指挥。年,26岁的穆蒂一举斩获意大利“圭多·坎泰利”指挥大赛首奖。年,他应邀出任佛罗伦萨节日歌剧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直至年。年,在赫伯特·冯·卡拉扬的提携下,穆蒂第一次受邀出现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并首度获得指挥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机会。自那以后,他便开始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愉快的合作关系延续了40逾年之久,穆蒂后来更有幸获颁维也纳爱乐乐团所授予他的“金指环”殊荣。2.总监生涯年,年迈的指挥大师奥托·克伦佩勒钦点穆蒂接班由他一手创建的英国爱乐乐团(新爱乐乐团)。在爱乐乐团任职艺术总监的接近10年时间,是穆蒂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家日益声名鹊起、扬名立万的重要机遇期。这一时期,他指挥爱乐乐团为著名的EMI厂牌录制了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全集的唱片录音,不但为他自己,更为了这支乐团在整个古典乐界奠定良好的国际声誉做出了突出贡献。年,同样是受到了另外一位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的重托,穆蒂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了辛勤耕耘数10载的爱乐乐团,远渡重洋奔赴美洲大陆开始拓展自己全新的个人艺术版图。匈牙利人奥曼迪将自己统领了40年的费城管弦乐团交接给了当时正值青壮年时期的穆蒂,殊不知,已然远在大洋彼岸的穆蒂一直显得有些“人在曹营心在汉”,虽然人在美国却又心系欧洲。此外,穆蒂也没能听从前任乐团总监奥曼迪的叮嘱,老人家临终前曾嘱咐他要把全部精力都专注在对于费城管弦乐团的建设和发展上。尽管如此,在费城-的12年任期里,穆蒂重塑了举世闻名的“费城之声”,并指挥乐团在PHILIPS厂牌下录制出勃拉姆斯全部四首交响曲、女高音狂想曲以及所有序曲的唱片录音。与此同时,还在EMI厂牌下重录了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全集,而且还极具胆识和前瞻性地录制了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交响曲全集的唱片。而对于雷斯皮基《罗马三部曲》、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普罗科菲耶夫《第三交响曲“火天使”》和《第五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等晚期浪漫派作曲家的重要作品,穆蒂在这一时期也多有涉猎、成绩斐然。年,已经在海外,包括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大陆以及美洲大陆都功成名就的穆蒂荣归故里,接任同僚指挥家阿巴多,成为著名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艺术总监。众所周知,纵使穆蒂与斯卡拉歌剧院在年末闹得不欢而散,而且最终还是以他本人的主动请辞作为结局来收场,但毋庸置疑的是穆蒂19年的斯卡拉歌剧院总监任期依旧是他职业指挥家生涯的巅峰时刻。时至至今,穆蒂离开米兰已有整整10年时间了,被这里的歌剧院伤透了心的他,宣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斯卡拉去指挥。可是,穆蒂却自始至终都丝毫不否认,在斯卡拉歌剧院的19载岁月无疑曾经是他个人履历表上极其宝贵且浓墨重彩的一笔……3.客席生涯除了自己辛勤耕耘了19年的斯卡拉歌剧院和歌剧院管弦乐团外,穆蒂与维也纳爱乐乐团之间超过40年的亲密互动同样是他逾50年指挥家职业生涯值得大书特书的精彩一页。穆蒂曾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PHILIPS厂牌录制过几张莫扎特的交响曲唱片,以及舒曼的全部四首交响曲。另外,在EMI厂牌他指挥乐团录制了舒伯特交响曲全集的唱片录音。穆蒂还曾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过多次欧洲巡演,其中包括年、年在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出。年,他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做日本巡演,时任乐队首席在巡演期间突发意外状况,从山上失足摔下并身亡,日本ALTUS厂牌所出版的当年穆蒂指挥乐团在东京音乐会现场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实况SACD录音,真实记录下了该名不幸罹难的乐队首席生前的最后一次参演……当年,穆蒂是因为受到了柏林爱乐乐团时任总监卡拉扬的提携,才有了一举登台初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机会。所以,穆蒂与卡拉扬以及他的继任者阿巴多所在的柏林爱乐乐团也一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穆蒂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最为频繁的时期,他指挥乐团为EMI录制了亨德尔和维瓦尔第这两位巴洛克时代最为重要的作曲家代表作,以及安东·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浪漫”》和《第六交响曲》,同时他还指挥乐团在PHILIPS录制出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在意大利》和《唐璜》的唱片录音。不过,自打年卡拉扬从柏林爱乐乐团总监职位上卸任继而离世,在由乐团全体团员票选出意大利人阿巴多作为继任者后,穆蒂便鲜少再与乐团合作了,毕竟当年他也与阿巴多一样是准备给卡拉扬接班的继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位置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之一。穆蒂除了曾在佛罗伦萨、伦敦、费城、米兰常驻以及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两支乐团长期保持紧密合作外,每年他还会作为客座指挥在慕尼黑、巴黎、纽约等地登台,与包括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在内的一线乐团合作上演音乐会。步入新世纪后,穆蒂曾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合作为EMI录制了凯鲁比尼《安魂曲》,指挥法国国家管弦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的现场实况音乐会唱片录音由NAIVE厂牌录制并出版发行。4.个人艺术穆蒂这个人,终其一生都无限推崇前辈大师指挥艺术的精髓,通过他们留存在世的唱片录音和影像资料,青年时代的穆蒂从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和富特文格勒等前辈大师身上吸收了许多养分、汲取了很多有益的东西。穆蒂曾表示说,他最为看重托斯卡尼尼指挥时百分百忠实于原谱的严谨态度与精确性;但与此同时,他亦十分欣赏富特文格勒处理音乐时的那份自在与洒脱。不过总体看来,穆蒂的个人演绎风格以及针对作品的诠释路数似乎还是更贴近于他的意大利同侪托斯卡尼尼。对待音乐作品极度严苛的客观主义进路以及百分之百忠于谱面的严肃艺术态度,显而易见都是继承了托氏之衣钵,这是托斯卡尼尼和穆蒂前后两代意大利指挥家在艺术取向上有别于他国指挥家鲜明的个性化共同特点。在传承并发扬了前辈大师指挥艺术精华的同时,穆蒂依靠其自身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偶像魅力,加之凭借其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为艺态度;在年初同辈的阿巴多往生后,如今他已经晋身为意大利学派指挥艺术在当下硕果仅存的“活化石”,受到了来自全世界范围内乐迷和观众的一致推崇与拥戴。在谢绝了来自纽约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任职的邀请后,穆蒂于年5月5日出人意料地欣然接受了来自另一支美国“五大”之一,芝加哥交响乐团艺术总监职位的盛情邀约。两者最初所签订的为期五年的合同,从-年度乐团音乐季开始正式生效,自接手芝加哥交响乐团起,年届七旬的穆蒂似乎又开始焕发出个人指挥生涯的第二春。按照合同规定,他每个乐季在芝加哥指挥10周,至今已经带领乐团走过了整整六个音乐季,上演了无数激动人心的音乐会;并在CSOResound的芝加哥交响乐团自有厂牌下出版发行了威尔第《安魂曲》、《奥赛罗》和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茱莉亚》以及柏辽兹《幻想交响曲》的现场实况演出唱片录音。年10月,在几经波折后,穆蒂接受了来自罗马歌剧院“终生指挥”的头衔。他对外宣布,往后将会把自己每年指挥歌剧演出的次数缩减至一次到两次,而他会把这仅有的机会都留给自己所任职的罗马歌剧院和芝加哥交响乐团两家机构。里卡多·穆蒂(RiccardoMuti)一直以来都是指引我真正亲近古典音乐的重要引路人,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是对他满怀感激与钦佩之情的。在我的固有印象里,穆蒂就是一名长发飘逸的意大利美男子,影像记录里的他永远都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帝王”之相,在这一点上,穆蒂与他所满心推崇的20世纪意大利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几乎是由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爱乐的整整12年时间里,我从全世界各地收集到超过张穆蒂的唱片录音。无论是他指挥英国的爱乐乐团为EMI厂牌所录制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全集,还是他指挥费城管弦乐团为Philips厂牌所录制的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以及他那极具代表性的斯克里亚宾交响曲全集,从录音本身的质量上来看,都实属佳作佳演无疑。5.穆蒂自述三年前,里卡多·穆蒂因病错过了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亚洲巡演,1月24日晚上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他在全场20多家媒体的静候与簇拥之下,终于平生第一次莅临国家大剧院。作为针对大师群访提问环节的预热,穆蒂首先在讲台上当着在场的京城20多家媒体记者朋友的面,说了一段开场白。穆蒂是这么说的,“我对于能够首度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这支全世界最好的乐团造访国家大剧院这样一座,无论是从其恢宏的建筑设计艺术本身,还是自打它开幕八年以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上看来都独树一帜的国家级艺术表演中心,而感到由衷地开心和高兴。我认为,芝加哥交响乐团是一支有着深厚积淀与传统的“马勒乐团”,在演奏马勒交响曲这方面,芝加哥交响乐团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亚洲巡演的曲目安排里有一首德国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的《为铜管和弦乐而作的协奏曲》,这部作品非常有意思,但其实演奏起来的难度可谓是相当之大。因为它既能够全面展示出乐团那闻名于世的铜管声部,又得以表现出乐团弦乐声部的不俗实力。要知道,稍早前我刚刚率团在台北、东京以及上海三地演出了六场音乐会,欣德米特的这部作品在每一地的演出过后都一时之间成为了当地舆论、媒体和观众争相热议的热门话题。而与欣德米特的该作正好相反,在我们这次的巡演曲目里,我还特意给亚洲观众准备了一首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交响曲“古典”》。普氏该作无疑是一曲相当轻巧、动听的仿古、戏谑之作,但如果仅就演奏技法而言,此曲其实也同样对乐团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高难度和严要求,尤其是芝加哥交响乐团那些乐队里的年轻音乐家可以通过对它的理解与演奏得到充分的锻炼,并且从中迅速积累到乐队合奏的实战经验。”6.记者提问大师的一番自我陈述后,很快就到了在场媒体记者的群访提问环节,但群访一开始,第一名记者的提问就不禁造成了一个小误会、小插曲。负责担任穆蒂英文翻译的那位与他一同坐在台上的先生,不知为何将该名记者中文原意为“当年离开罗马歌剧院后,请问您从罗马把什么宝贵的经验带到了芝加哥吗?”,误译成,“您作为一名从意大利来的指挥家是怎么在北美新大陆开展您个人指挥生涯新事业的?”。显然,穆蒂有点被身旁这位先生的翻译给惊吓到了,大师顿了顿,然后开始批评和指正这一问题本身所存在的逻辑错误。他说,“作为意大利指挥家并不是就只有指挥意大利作品的份,也就是说,并非德国人就只能够演奏德奥音乐,法国人就只能够演奏法国音乐。因为假如按照这一逻辑,那岂不是作为中国人就根本不配演奏任何古典音乐作品了吗?你们需要知道,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家是不分国籍的。意大利指挥家阿图尔·托斯卡尼尼就不啻为是一名伟大的瓦格纳音乐指挥家,而德国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不也同样指挥意大利歌剧音乐吗?”所幸的是,坐在场外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华人中提琴副首席张立国先生及时又追问了一遍该名记者所提出问题的中文原意,并重新用英文翻译给穆蒂听。恍然大悟的大师这才长抒了一口气,他唯有不厌其烦地补充道,“我承认自己的确是从罗马歌剧院把意大利文化带到了芝加哥,并将我个人的意大利背景融入到这支建团历史长达周年的优秀乐团的艺术生命当中,而且还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在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历任音乐总监里,弗里茨·莱纳和乔治·索尔蒂爵士都是匈牙利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在阿根廷出生的以色列犹太人,拉法尔·库贝利克则是捷克人,让·马蒂农是法国人,而我是意大利人。其实意大利的声音就是欧洲的声音,但假如硬是要争论,那意大利的声音也只不过就是略微带有一点方言味道的欧洲之声罢了。从我在过去几年的音乐总监任期经历上看来,芝加哥交响乐团如今所能发出的声音,显而易见地是在歌唱性这块上相较以往有了一个大幅提升,毕竟意大利的声音就是歌唱之声,或曰歌剧之声。”紧接着,第二名记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她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先前您曾两度来中国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并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都登台演出过,那么请问您对中国以及中国观众都有什么样的评价?”。穆蒂感叹道,“不知为何无论走到哪里,亚洲人都总是喜欢问我,关于如何评价亚洲人的这一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所认识的观众只有两种:一种是聪慧的、尊重艺术的、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好观众;另一种就是不那么聪慧的、没那么尊重艺术、不会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不那么好的观众。不但台下的观众如此,场上的音乐家也如出一辙。也许你们在座的各位不知道,即使是欧洲乐团也有把歌剧作品演得十分糟糕的时候,但反观我曾经两度指挥过的上海交响乐团,他们团毫无疑问有着优秀的音乐家,同时这些音乐家还都善于在排练和演出前做足充分的准备,而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除此以外,目前的国外歌剧制作领域存在着一个不良现状,那就是人们在对待莫扎特、理查·施特劳斯和瓦格纳的歌剧制作时都显得尤为严肃,但一转到意大利歌剧制作上就开始变得庸俗不堪。像《阿依达》这样的歌剧剧目都已经沦为歌唱家为了一昧讨好观众、震慑观众,单纯只是片面追求演出效果的个人秀场。作为意大利歌剧制作如今堕落至此,面临日益走向低俗化的这一趋势着实是不应该的啊。因为意大利歌剧的演出绝不仅仅只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个观演的好印象和注重演出效果那么简单。朱塞佩·威尔第曾经说过一句话,对于歌剧这门艺术而言,只有一个创世者,那便是作曲家。托斯卡尼尼曾与威尔第一起工作过,所以他一直牢记着威尔第的这句话,而我的老师是托斯卡尼尼的助手,他把这种完全尊崇作曲家的乐谱指示与标识的绝对客观主义的艺术原则传给了我。在托斯卡尼尼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到意大利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政权的排挤,而被迫离开意大利之后。像《弄臣》这样的威尔第歌剧,在意大利本土开始被拉长线条来演唱,并开始带有强烈的戏剧化倾向。不过当我在年开始走马上任斯卡拉歌剧院艺术总监之后,我便开始硬性要求歌唱家在舞台上演出《茶花女》、《弄臣》和《游吟诗人》这样的威尔第传统歌剧剧目时,都必须严格按照作曲家总谱的指示和标识,来墨守陈规、中规中矩地完成演唱。”7.我的问题很快的,作为媒体记者提问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来了,作为我自己终于有幸成为提问人。而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自伦纳德·伯恩斯坦时代的大力推动开始,尤其是在这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仿佛如同作曲家本人所说的那样,我(古斯塔夫·马勒)的时代终将来临,毋庸置疑的是马勒的时代确实已经到来了。放眼当今的国际古典音乐界,几乎再也没有任何一名指挥家或者说是乐团,会像当年的富特文格勒与柏林爱乐那样对马勒的交响曲置若罔闻了吧。众所周知,作为您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马勒交响曲演释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您就曾指挥费城管弦乐团为EMI唱片公司录制过一版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也就是您即将于明晚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为北京观众所带来的“马一”。与此同时,上世纪90年代,您还曾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留下过一版马勒《第四交响曲》现场音乐会的实况演出DVD。可是,除了“马一”和“马四”之外,似乎您就再也没有触碰过任何作曲家其他同等重要的交响曲作品了。那么,请问作为观众的我们是否还有理由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您有可能会把自己针对作曲家马勒的个人理解、演绎及诠释延伸、拓展至他第一和第四以外的其余七部交响曲当中呢?要知道,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荣誉指挥,刚刚过世的法国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就是一位全面的马勒权威啊。此外,我还听说同样也是不久前才刚去世的著名美国业余指挥家卡普兰还曾在您当年演出“马四”的当晚,就作品第一乐章开头长笛独奏片段的节奏问题给予您友好的提示与建议,而在音乐会结束后,您甚至于还主动找到他并向他表达了谢意呢。”针对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穆蒂先是会心一笑,他试图纠正我说,“我还曾与包括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克里斯蒂娜·路德维希在内的众多歌唱家合作演出过马勒的全套声乐作品呢,这点恐怕连你也不知道了吧?”。然后,穆蒂就开始点名了,他说,“像富特文格勒、约瑟夫·凯尔伯特、塞尔吉·切利比达克和沃尔夫刚·萨瓦利希这样的指挥,一辈子碰都没碰过马勒的交响曲。作为我自己,无论如何都至少还保有两部马勒的交响曲作品可供排演吧?”穆蒂面对着我,开始郑重其事地说道,“人类的生命何其短暂,但西方古典音乐长河里的保留曲目又浩如烟海,所以并不是我主观上不喜欢哪部作品,而是客观上要求我必须坚定地做出选择;何况对我来说,也只有是在做足了充分准备,并确信自己委实吃透了一部作品之后,才得以有效地进行排演的。你们在座的各位得知道,我个人作为一名指挥家的保留曲目,从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的蒙特威尔第作品,一路延伸到当代美国作曲家梅森·贝茨(MasonBates)的作品呢。虽然我只指挥过马勒交响曲里的“马一”和“马四”两部作曲,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来,我把自己有限人生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推介诸如意大利作曲家布索尼、马尔图奇、卡塞拉,乃至于还有普契尼罕见的管弦乐作品以及我的老师尼诺·罗塔的电影配乐作品当中了啊。”最后,大师还不忘开了句玩笑话,“假如我能够活得再长久一点,那么或许我还倒真有可能帮你实现你个人的愿望,去尝试指挥更多的马勒交响曲作品。”通过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提问,以及穆蒂本人耐心而详尽的解答,一时间他回答问题时所流露出的亢奋劲儿和激动情绪似乎都被有效地带动开来,在主持人宣布本场群访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他执意再让他所看到的一名台下的女记者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古典音乐与现代文明”,尤其是在当下普遍面临“世界危机”威胁时所具备的功能和作用。穆蒂说,“音乐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以往曾经带领斯卡拉歌剧院管弦乐团冒着危险前往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后的废墟城市萨拉热窝去演出,与那里的难民一起演奏。与此同时,由我所倡导的这一项目,三年前还被带到了非洲国家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在那里我指挥多名当地的小孩子演出威尔第的歌剧《纳布科》,我被他们当时那份对待歌剧艺术的全神贯注、孜孜不倦所深深打动。”音乐无国籍(Musichasnonationality),这是穆蒂在这次媒体记者的群访活动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一句话。“因为音乐的存在,我们这整个世界都仿佛变成了一家人。作为每个人都会是有一点正义的,如果一人一点小小的正义,累积起来的话,这整个当下世界的现实危机也便迎刃而解了。”在群访结束后,台下观众凑过去找大师合影的空隙,我上前去在争得穆蒂的同意后,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在您作为一名客席指挥家的职业生涯里,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两部热门作曲家的冷门作品受到了您极大的青睐,在与包括柏林爱乐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等对您来说最为重要的几个一线乐团的演出合作当中,您曾多次将这两部作品搬上客座音乐会的舞台。其一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在意大利》(AusItalia),从前您还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Philips唱片公司留下过该曲的录音;其二则是安东尼·德沃夏克的《第五交响曲》。所以,可以请您聊一聊关于这两部热门作曲家的冷门作品吗,还有您自己是否对这两部作品抱持有格外特殊的感情呢?”在听到我的提问后,大师随即是一脸的欣喜,他很快回答道,“理查·施特劳斯的这部作品是他在二十二三岁青年时代的早期作品,作品里他通过他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直观地描绘出他所亲眼目睹到的意大利风土人情。至于作为我自己则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所以指挥这部作品我想也是理所应当、顺理成章的吧。当然了,其实这部作品最早还是著名的前苏联钢琴家斯维尔托斯拉夫·里赫特推介给我的呢!”这时,我插话说道,“在去年您重回柏林爱乐大厅,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部作品前,在柏林爱乐乐团官方网站的数字音乐厅(DigitalConcertHall)放出的一段针对您的专访中,就有您专门讲述的关于里赫特的推介以及这部作品由来的那个故事。”殊不知,穆蒂顿时笑得前仰后翻,还拿自己的右手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左肩,面带喜色地“抱怨着”说,“你小子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不得了啊不得了……”8.演出观感就在前一天,听我一位专程从武汉赶到上海听了大师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沪上第二场音乐会的朋友说,“穆蒂当晚对于“贝五”第二、三乐章的处理有一种歌剧化的渲染,好比是对于一出意大利歌剧开场前的气氛烘托。那种歌唱性的抒情感觉听之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我个人在之前对于“贝五”的聆听经历当中所从未有过的。”此外他还告诉我,“大师对于“马一”第三乐章的处理,听起来叫人依稀有种芭蕾音乐的感受。”在国家大剧院当晚针对穆蒂的群访,对我来说是获益匪浅的。在群访结束后,离开国家大剧院回家的路上,我都一直保有一种难以名状、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与触动之感。只因为在这一天,我终于梦想成真般地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偶像,并三生有幸地得以跟他面对面交流、问答,乃至于相互开玩笑,可谓嬉笑怒骂尽在其中了……遗憾的是,梦想总是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乃至于有时候当梦想照进现实,最后带给你的恰恰不是心满意足,而是曲终人散后的不解和无奈。穆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在北京的两场音乐会,我都深表疑虑,并且大为不满。从前那个指挥台上生机勃勃的意大利美男子似乎已经活力不再,穆蒂指挥时的动作、手势都被过度简化了,而这不知是出于他自身的年老力衰,还是由于他本人如今日渐慵懒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穆蒂在北京的两晚演出当中所诠释出的“贝五”、“马一”以及“柴四”都是远远背离作曲家创作初衷与本意的演绎。我想这种对于经典作品艺术风格拿捏上的重大偏差,已经与作为一名指挥家的音乐品味和艺术个性无关了。因为这种对于早已盖棺定论的经典曲目,在其艺术风格把握上的严重失误,在我看来,其实已经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弥天大错了……(全文毕)欢迎转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baojieshaobj.com/wltq/583.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国留学十大租房网站汇总不得不看的指南
- 下一篇文章: 7月新番ChaosDragon赤龙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