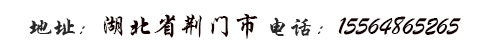10倍速疗法第六章肯定一个人的改变
|
第六章肯定一个人的改变——卞新仁大夫 有一个看来矛盾的现象,就是某些病人来寻求心理治疗,并不是因为遇到负面的问题,而是在人生经验和生活环境交相影响下,发生正向的人格改变,反而因此感到焦虑。虽然他们喜欢自我的新体验,但由于这个新体验和原有维持自我价值感的方式发生冲突,而觉得焦虑。在这种情形下,治疗的重点就要放在帮助病人了解这个冲突的本质,进而能适当的处理。 卞新仁大夫 当他打电话来约诊的时候,我只觉得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但不太确定是谁。直到卞新仁大大出现在诊疗室时我才想起来,四、五年前我为内科和家庭医学科医师所办的心理治疗讲习会,他是成员之一。卞医师的穿著讲究,运动员的体型加上英俊的外貌,使他看起来比六十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他说来找我的原因是:“我需要和一个人谈谈看,好知道我是不是需要和人谈一谈。” 病:你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啊,在精神科医师面前不该随便用这个字眼!我的意思是,你可能无法相信这种事。 治:嗯,让我听听看,你继续说。 病:要从六个月前说起。那是一个礼拜五晚上,我必须参加一个会议,太太也有事要出去,由于不想开两辆车去市区,就约好等她办完事来接我回家。因为走路太远了,所以下班后我必须坐出租车去开会。 治:我了解。 病:下午五点半正好是交通尖峰时间,一大堆人都在等出租车,每一辆出租车都坐了人。等了一会儿,我只好用走的,并想着也许可以在半路上叫到出租车。过了几个路口,我看到一栋辨公大楼前有几辆等着载客的出租车,于是向那儿走去。当然啦,等我走到时,那些车已经栽客离去,但我想在那儿等出租车可能比较容易。没几分钟,就有一辆空车开过来,我伸手招呼的同时,一位年轻妇人靠过来,不太高兴地对我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清楚,只听见:“排队”两个字。我向她道歉说:“喔,我插队了吗?这儿等出租车是不是要排队?” 她很坚定地说:“没有,但是我先到的。”我猜她可能在我右边等,所以看得到我,而我没有看到她。我决定把这辆车礼让给她,顺口问她往哪个方向走。她说向北,我说我也是。我们很快就同意共乘并分摊费用。我会先到目的地,而她还要再过几个街口才下车。上车后,她整个人缩在左侧靠着车门,我也接受她的暗示,紧靠右侧,她把名牌大皮包放在我们中间。客气地坐定后,我们互望了一眼,这是我们第一次看清楚对方。 我不知道她看到我时在想什么,可是……你看不看歌剧? 治:有时候会看。 病:有没有看过唐帕斯癸这部歌剧?(译往:《唐帕斯癸》(DonPasquale)是意大利名歌剧家多尼兹提(Donizetti)所编之知名喜剧。主角唐帕斯癸是一个富有而乖戾的老光棍,他不曾亲眼见过诺瑞娜(Norina)这个美丽、聪明的年轻寡妇,却不准侄子俄聂斯托(Ernsto)娶她。有一个医生马拉泰塔(Malatesta)是他们的朋友,同情这一对年轻人,于是建议唐帕斯癸娶苏芳妮亚,骗他说是自己的妹妹,其实苏芳妮亚是由诺瑞娜假扮的。他们的婚礼以荒谬的方式进行,要显出苏芳妮亚有多卑鄙,会让唐帕斯癸下半辈子水深火热,并花尽他所有的钱。马拉泰塔建议被吓坏的唐帕斯癸不要完婚,这时俄聂斯托勇敢地代替伯父迎娶苏芳妮亚。后来唐帕斯癸知道自己被愚弄以后,仍然祝福这对年轻的新人。) 治:我爱死它了!虽然懂音乐的朋友都叫我不要看,但只要一有演出,我绝不放过去看的机会。 病:我也是,那你一定知道当诺瑞娜假扮的苏芳妮亚掀起面纱时,唐帕斯癸又惊又喜、喘不过气的样子啰? 治:我印象深刻。 病:那就是我当时的经验!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脸庞非常迷人,没有化妆,有一点暴牙——但我很喜欢,金色的头发垂到领子,恰好衬托出脸型。那张清新、年轻的脸够资格被刊登在杂志封面,我甚至一时怀疑她就是某位时装模特儿。她露出来的小腿也很美,可是我想她的身高还不够当模特儿。接着我看了看她的手,没有结婚或订婚戒指。 我问她:“妳在那栋大楼上班吗?”并向她解释我从办公室走了一段路在找出租车,对刚才的环境不熟,才会冒失地抢在她前面拦出租车。 她说:“对,我的辨公室在那里。真高兴今天是星期五,下班就放假了。” “喔?妳从事哪一行?” “我是律师。”她边说边对我微笑,我想她是对刚才不客气的态度表示歉意,也可能意谓着她还是新手,对自己的头衔不太习惯。 “你专攻哪一方面?” “我主要处理债信重整和商业重建,就是专门处理破产方面的问题。你呢?” “我是医生,心脏科专科医师。” “我想你的工作也不轻松。” “没错,工作很辛苦,但很值得。我们现在可以为病人做许多先进的治疗。” 谈话中断了一阵子。我心里想着,命运把我带到这个美丽的女人旁边,她是我所见过最吸引人的女人,既聪明、自在,又友善、迷人。三十年前你在哪里?不要这么久,十年前能遇到就好了。就像唐帕斯癸说的,我现在已经老了,我是个垂涎和我女儿差不多年龄女人的老头子。如果我问她的名字,她一定会生气地拒绝;如果我把名片给她,也不过是多了一个她和男朋友聊天的话题,徒然留下老牛想吃嫩草的笑柄罢了,我还是庄重一点的好,我心里想着。 她先打破沉默微笑问我:“你执业多久了?”天啊!难道她能看透我在想什么吗? 我微笑回礼,心里想着:我执业三十多年了,刚入这一行的时候,你恐怕还没出生吧。 “嗯,我估计差不多二十八年了吧。” 我想一切就到此为止吧,如果之前还不够明确的话,我和她年纪的差距就够吓倒她了。我反问:“妳这么年轻,应该还不是合伙人,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升上去?” “你好像满懂法律界的事嘛!” “当然了,我有好几个朋友和病人都是律师。” “嗯,你说的没错,如果我不跳槽的话,也还得再努力几年才行。” “妳可能跳槽?” “不一定。” 我不敢问她对婚姻的计划。她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想钓她的登徒子,问这种问题只会让自己被别人瞧不起罢了。 她说:“今晚塞车塞得好厉害。” “对,一点也没错。”我同意她的看法。我第一次为了塞车感到高兴。但是到我下车前,彼此也没再深入谈什么。 “医生,你到这里看朋友吗?” “不,我今晚在这里开会。” “在礼拜五晚上?” “对啊,周末晚上还不能休息,真令人讨厌。” 多刺激啊,电影中的谢瓦利(译注:谢瓦利(MauriceChevalier)是法国名演员及歌唱家,三〇到五〇年代期间,在美国以迷人讨喜的花花公子形象,演出多部电影。)在这种情形下一定会说:“妳说的一点也没错,我真正想做的是带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去跳舞,你愿意让我美梦成真吗?”他到死都过着这种浪漫的生活。而我却十足是个懦夫,真是该死! 她的手在皮包里掏钱,一副准备和我讨论如何分摊出租车费的样子。我拿出皮夹,掏出一张五元钞票和几个零钱,比我刚才坐那一段路的费用还多一些,我说:“这一段都我出。”随即把钱放进她打开的皮包。她大概是为了我不只付该付的那一半,而露出惊讶的表情吧,她心里可能想着:“他真是个老好人,就像慷慨的老爸一样。”“请你停在这里。”我开门下车,微笑和她道别:“再见,律师,很高兴认识妳,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你真好……谢谢你……祝你开会愉快。” 整个晚上开会我都心不在焉,一直回想着和她相遇的过程。我太太开车载我回家时,我也一语不发,但她没有发现什么异状。我们除了小孩和房子的问题以外,已经很久都无话可谈了。我本来以为晚上会失眠,可是没有,我睡得很好。星期六我必须去一趟办公室,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才发现皮夹不见了。翻遍了之前穿的衣服都找不到,我沿着前晚走过的路寻找,在前门、车库也都找不到,最后一个可能是:在我昨晚穿过的雨衣里。但奇怪的是,我在口袋里只找到一些零钱,却没有皮夹的影子,它真的不翼而飞了。但这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我平常不会带很多钱在身上,信用卡只要打个电话挂失就好了,而我至少有一打以上的皮夹,是历年圣诞节和生日礼物累积下来的。我顺手抓了一个皮夹,再从太太的皮包拿了一些零钱就出门了。 开车时,我还一直回想昨晚邂逅她的经过。一到办公室忙碌起来,就不再为这件事萦怀了。在内心火热让我感到难受之前,我用忙碌来化解自己一直去想“我昨晚应该怎么样”、“我怎么没有表达什么”的苦恼。我太了解这种感觉了。礼拜天我照例看看报纸,在家做一些杂事就过去了。 礼拜一我先到监理站申请补发驾驶执照。那一天真是忙碌,虽然希望有点空闲回味一下和她相遇的经过,但除了工作,我什么也没想。一直到五点左右,秘书告诉我有一个人拿着我的皮夹要还我,我才惊觉最后一次看到皮夹时是在出租车上;天杀的,一定是司机捡到了,他不交给警局招领,却直接找上门来,大概是想得到一点酬劳吧。 我告诉秘书:“请他进来。”我这时感到双重的焦躁,他的拖延害我增加不少麻烦,而现在我还得花点钱向他致谢,简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你知道吗,走进来的竟然是她!那时候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感受,我敢说,在那一刻里,我整个生命都被照亮了!我平常不善言辞,但那时我听到自己毫不犹豫,也不结巴,发自内心向她说:“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彼此靠近、拥抱、亲吻,不是很激烈,但也不是一般礼貌性的拥吻。那时两人已认定了彼此相属。 她问:“现在我们该怎么辨?” 我说:“一起去吃晚餐。既然妳知道我的名字,我还不知道妳的,而我还没有拿到皮夹,就让我来选餐厅,你请客好了。” 你知道吗,从那一刻起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可爱的小律师走进我的生命!你看我到现在还不敢把她的名字说出来,因为生怕如此一来,一切会像梦一样烟消云散。我已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我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个寡言、疏远,甚至自大,不爱说什么话的人。虽然我值得信赖,也算是个好人,但我对人不够热诚,从来不积极拓展人际关系。也由于我的个性使然,有的病人不愿意找我,我自己知道。可是忽然我变成像谢瓦利一样迷人、有吸引力,生活变得充实。我的年纪反而成为一种魅力,也不知何故,我开始注意每件事美好的一面。今天我已变成自己一直幻想成为的那种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事:我非常爱她,更重要的是,同时我也爱我自己。 治:听起来很动人。 病:不只是这样,下面的你一定很想听。爱莉和我——(微笑)告诉你应该很安全,她叫班爱莉——我们去一家很棒的咖啡馆坐着,那里很安静隐秘。我们点了葡萄酒,静静地凝视着对方,像两个魂不守舍的年轻人一样。我想自己最好说点话,就说:“我从来没有为了掉皮夹而这么快乐过。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掉皮夹,我从未遗失过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掉,妳是在车厢里看到的吗?”她说:“不,我的爱人,你没有遗失皮夹。”“爱人”这两字让我至少心跳加速了一倍。我的胸口一紧,差点就心脏病发作。 “我没有遗失皮夹?” “你那时打开皮夹,拿出一些钱塞进口袋里,然后把皮夹丢进我的大皮包里。” “完全是佛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的疏忽。” “我也是,事后我才想起自己眼睁睁看着你把皮夹丢到我的皮包里,当时却没放在心上。直到出租车开到家门,我还一直在想着你,付钱给司机时,也没有注意到你的皮夹。一直到今天早上,我打开皮包看到你的皮夹时,你把皮夹丢进皮包里的整幕景像才浮现眼前,这时我才知道坐在车上相遇的那几分钟,你和我一样因为对方而魂不守舍。之后一切就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了。”“我实在太高兴了。” 葡萄酒刚好送来,我们举杯不约而同地说:“敬佛洛伊德。” 卞医师说到这里停下来,满心期待的看着我。我该说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他正面的力量:他是个有成就、有能力的心脏科专家,他对自己的情绪很清楚,也能分析自己的情绪,叙述的能力也很好。但是,他为什么要来我这里?不论是自主性、情感/理智还是创造力,他每一个环节看起来都很好。他所谈的事情没有涉及和心性发展环节有关的事,但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人通常不会像他这般口若悬河、单刀直入地把自己的事情交待得一清二楚。至于依附环节,他的婚姻显然完全不能满足他,但如果透过班爱莉已得到解决的话,他又何必来找我呢? 从正向移情关系的角度,我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他在几年前听过我的演讲,光是这样的接触就足以趋使他来找我,表示他和人产生正向连结的力量很强。他能以这么放心的态度来谈这件改变他一生的事情,表示他与人亲和的能力很好,也表示他愿意信赖我。他和我交换对多尼兹提歌剧的看法,是想肯定和我之间的关系够不够。他问我熟不熟悉唐帕斯癸时,我可以简单回答就好了,但他的活力可能会因为简单的回答“是”而泄气,所以我选择详细说出自己的看法。这么做或许能加强我们之间的连结,但他也可能对我的品味表示不屑,不管他如何反应,我都可以藉此评估他如何看待与我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对这出歌剧不熟,也不会只简单回答“不知道”,我可能会说:“我不清楚,也许我看过,但是没什么印象。你愿不愿意说一说这部歌剧和你现在要谈的事有什么关联呢?”藉此加强我和他的亲和关系,而我所表达的兴趣,也可以成为我和他之间有所连结的因素。他谈到一半时,克服自己的担心而说出恋人的名字,表示他已经完全信赖我能帮助他。但问题是,要帮助他什么?我当前要做的,是厘清他有什么问题需要藉助心理治疗来处理。 治:你看起来既快乐又充满活力,但我还不清楚你寻求心理治疗是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部分我需要再多了解一下。 病:嗯,我还以为你已经很清楚了。不知道是什么事让我觉得很焦虑。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但内心就是有些不舒服,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治:你现在与太太和恋人相处的情形怎么样? 病:我每天都和爱莉见面,只要有机会就和她共度周末。前一阵子借着开学术研讨会,和她一起去加州玩了一个礼拜。老实告诉你,研讨会我几乎没有参加。和她在一起实在太棒了,我很希望能搬出去和她同居,可是律师告诉我在分配好财产之前,绝对不要搬出去。 治:你已经和太太讨论离婚的问题了? 病:对,和爱莉在一起没几个礼拜,我就向太太提出离婚的要求。我从头说好了。那天晚餐后,我和爱莉一起回她家,我们一直聊天,彼此都提醒对方不要太鲁莽,但我们越聊就越清楚,彼此都想和对方在一起。虽然我们像青少年那样亲热、相拥,但双方都了解面对的是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没有上床。一直聊到清晨四点我才离开,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治:太太呢?你这么晚才回去,她怎么说? 病: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回来的声音,我们分房好几年了。我晚上常常不回家,她早上多半睡得很晚。她如果看我不在,会以为我很早就出门了。有时她会疑神疑鬼的,为了预防这种情形,我会在俱乐部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 治:你已经向她提出离婚的要求吗? 病:当然,但不是马上就提出。爱莉和我一直在一起,我们试着去看一些现实的问题。我问她,彼此相差三十二岁,如果她想要小孩,我恐怕没有办法活到小孩长大成人;就算不要小孩,她等于把青春耗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到中年时就成了寡妇。如果我老不死的话,她就得赔上自己的壮年来照顾我,她不需要做这种牺牲。 但是爱莉认为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身体状况也比她之前小我一半的男朋友还好——我们相遇后一个礼拜,她就和这个男友分手了。况且她也不想要小孩,几年前她就结扎了。她的童年和我类似,缺少欢乐,也不得妈妈欢心。她辩说天知道谁会活得比较久,如果是她病了,我愿不愿意照顾她呢?我很肯定的告诉她:“愿意。”她还辩说,也许像我这样人生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觉得她太嫩而不愿共度一生。我告诉她,其实她的智慧远超过她的年龄,而且她太吸引我了。她还想知道钱的问题怎么办?身为一个律师,虽然不是婚姻法的专家,她也很清楚离婚时分财产的问题,如果我急着再婚的话,可能会被愤怒的前妻和精明的律师榨干。我说事实上我太太从她父亲那里得到大笔遣产,比我还富有,虽然如此,我们的财产一直是分开的,我也坚持家里的开销完全由我负担。我告诉爱莉,无论如何,即使法院判我要拿出一半财产给太太,剩下的钱也够我下半辈子花用。当一个人所拥有的只剩工作的时候,会发现迅速累积财富是很简单的事。 我们这样一来一往的,都在试图告诉对方,我们爱对方胜过一切。这显得很滑稽,我们忍不住爆笑起来,然后上床。我告诉你,对一个从来不曾和相爱的人做爱的人来说,那真是棒透了的经验! 过了几个礼拜,我告诉她很想和她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我要尽快办好离婚手续。想到自己以后可以拥有多么快乐的生活,我实在无法忍受继续住在现在的房子里。她说愿意嫁给我,我们现在正在计划婚礼。 治:你已经向太太提出离婚的要求吗? 病:对,差不多有三个月了。 治:她有什么反应呢? 病:除了生气,还会怎么样?可是听着,我知道这次会谈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该走了。下次什么时候可以见你?到时我想拿一样东西给你看。 卞大夫在第二次会谈时,带了一个棕色的塑料袋来。他坐下后,从里面拿出一只鞋子,指着靠近指尖一处快磨平的地方说:“你看到没?” 病:如果一张图像胜过千言万语的话,这只鞋子又胜过十张图像了。这是我每天用大脚趾在地上磨擦所造成的,大约三年要换一次鞋底。我就像这只鞋承受着长期的压力,住在一栋没有爱的房子里三十五年,她从来就不快乐,老是对我发脾气,我的家庭生活可以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学会什么问题也别问,避免任何可能的磨擦,这就是我的婚姻生活。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医生啊,我要求离婚的时候,她当然很生气,但她的生气,就如同以前我要求她吻我或做爱时的反应一样。 自从遇见爱莉以后,我不再拿鞋子发泄情绪了。医生,我是不可能回头的了。 治:你这样说,好像我在劝你回头似的。 病:(发现自己在生气)你说的没错,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生气。你给我不少帮助,上次谈完以后,我觉得很平静,今天我满怀希望来这里,可是没一会儿,我就觉得对你很生气。 治:我也觉得很奇怪,你的话听起来不只是生气,好像在防卫什么似的。你应该不是针对我,你觉得自己像是在对谁说话?现在在你面前的人好像谁吗? 病: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觉得生气了。 治:你把自己的婚姻生活描述得像地狱一样,那么当初为什么和她结婚呢?而且不要忘了,三十五年来你都是这样过的。 病:相信我,这三十五年来,我每天都想着要离婚。我当初是身不由己才踏上红毯,我订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现在对爱莉这般的感情。甚至可以说,在结婚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爱我太太。 治:那你是怎么遇到她,又身不由己的踏上红毯呢? 病:(陷入沉思,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出身贫穷,我们爱尔兰裔移民多半住在破旧小屋中,很少有中产阶级。我爸爸是个码头工人,和其他同事一样整日酗酒,但是他对我期望很高,希望我将来当律师。他所听过有来头的人,不是市议员就是国会议员,而这些人都是律师出身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能当律师。我对这一行没有兴趣,但是不能对爸爸说“不”,所以高中时他帮我安排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那儿工读时,我就去了。我很幸运,薛先生照亮了我的生活,他对我谆谆教诲,不会随便敷衍我,我想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我就像他一直想要而没有的儿子,而他就像父亲一样了解我、指导我,这是我亲爸爸无法做到的。 虽然我既努力又聪明,什么都肯做,但是我对律师这一行就是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薛先生怎么想。有一天他把我叫去,告诉我他认为我比较适合当医生。他这么说时,我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说的没错,由于父亲一直坚持我应该当律师,所以以前不曾想过自己适合做什么。薛先生说他会和我父亲谈,看看可以怎么帮我。到今天我还一直怀念他,他是我的恩人。薛先生的话对当时的爱尔兰人来说,可说是一言九鼎,只要他和我爸爸说就没问题了。他鼓励我拿到奖学金,由于我表现很好,申请到州立医学院就读。那时要想进医学院是很困难的…… 治:我记得申请的人数比学校的名额还多上七、八倍。 病:没错。他就像我第二个父亲一样,不像我爸爸——大声咆哮、醉倒酒国、常常被人嘲笑——而他却高贵、安静、严肃、不苟言笑,总知道怎样把事情处理好。我家很穷,但奇怪的是,以前老爸只要有钱一定会拿去买酒喝,可是在我打工的钱不够付学费时,爸总是拿得出钱来。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相信一定是薛先生给爸的,他一定很想拿去买酒,但如果薛先生交待了用途,我爸就不敢挪用。 有一次薛先生留我吃晚餐,就在那次我遇见了我太太。她是薛先生的独生女。有时我会猜他是故意安排的……但我实在不愿意这么想,这好像我成了耍猴戏中的布偶,任人摆布。不,我不相信,他绝不会把我当成给女儿的投资品,我相信他只是单纯地喜欢我,我相信他。 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我和她根本就没有恋爱的感觉,她也没有,但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在一起了。她要求的不多。一个医学生,没有多少时间约会,这一点我想你也了解。她从来就不会因为我为了准备考试、取消约会而生气;她也不会因为我迟到而拉下脸来。之后我才明白,她也希望我没时间陪她或约她;她父亲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也知道父亲希望在自己过世前看到她安安稳稳地结婚,而我就是她父亲中意的人。她也身不由己,就像我一样。 我相信我们结婚那天,是薛先生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我父母也觉得沾了不少光,爸爸不知道是被这种社交地位的提高吓到了,还是太高兴,整个礼拜都没有喝酒。到过世为止,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后来过世也不是因为酗酒造成的肝硬化,而是被一个松脱的箱子压死。 唯一不觉得高兴的,就是我和我太太,我们只是做别人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况且,既然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理所当然就会很好了。她对我不热情也就算了,但是一结婚她马上变得很冷淡、别扭,就和她妈妈一模一样——一个坏脾气的婊子,和薛先生完全相反——只关心事情的表面,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我很奇怪薛先生怎么能忍受他太太,也许他真的爱她,也许只是认为事情反正不会更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好了。结婚头几年我就是这种感觉。后来我开始行医,买了不错的房子,生活也无虞。薛先生在我太太名下存了许多钱,很明白地向我们表示,在他有生之年若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向他提出要求。在他和妻子死后,所有财产都会由我太太继承。 我猜自己觉得有义务照顾她吧。我开始赚钱后,所有家用都由我支付,她的钱都花在慈善事业、芭蕾表演等地方——就像佛洛斯特(Frost)所说“买来的友谊”一样。 治:继续说。 病:我一直很厌恶参加那些晚宴和舞会每个人都互吻一下,说“你好”和“再见”——真是真情的盛宴啊!这些人都心知肚明,在那里真正算数的是你有多少钱。不过当我了解到,这些富有却不快乐的人多么需要这种聚会后,比较能忍受穿着燕尾礼服去参加。感谢老天,我再也不用去了。还有就是,我不愿意伤害薛先生,一直到他过世,我都和他维持很好的情谊。我从来没向他抱怨,我猜他也知道这些事很无聊,但他就是这么过的,可能也从来没想到可以有别的生活方式。我一直相信我的忠诚对他很重要。 治:你们有小孩吗? 病:有,我们必须为他们生孙子。有两个女儿,她们和妈妈是一国的。从她们小时候起,太太就不让我照顾小孩,老是要我当个缺席的父亲。现在一个在法学院,另一个也在念大学,但还没决定自己的方向。我要求离婚,正好让她们认定我就是妈妈所说的那种不负责任的人,不会有人想听我的心声,她们只相信妈妈的片面之词。我原本希望我们一起向孩子解释这件事,但我太太不肯,两个女儿也没兴趣听我解释。 治:根据你刚才所说的,你太太虽然和你在一起并不快乐,还是为了你想离婚而生气。 病:(他讲得太入神了,没有听到我说的)我们两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可以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我是说真的,一句话都不说,连早安、晚安都不提。 治:你刚才说你太太为了你想离婚而生气。 病:对慈善团体、剧院、音乐厅来说,我和她出双入对,我们离婚的话,那些社交圈中的朋友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能告诉她,我根本不在意那些虚假的朋友怎么说。只要她还有钱——除非太阳打西边上来,她的钱才会用尽——那些马屁精会继续奉承、谄媚下去。万一他们提到我,她可以说我已是个老朽的男人,像老唐帕斯癸一样没有好结局。我已经尽够了义务,再也不要过这种生活了。 治:你不需要说服我什么。只要你自己相信应该这么做就好了。 病:你真的相信我吗? 治:我相信你,但是轮不到我来原谅你;这像是你现在所寻求的。可是你到底觉得冒犯了谁,你怕伤害到谁呢? 病:我并不觉得有罪恶感。但你说得对,我好像一直在辩解什么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会谈结束后,我认为病人的焦虑,和背叛已故岳父的托付有关,是依附环节中的冲突所造成的。但我并未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根据他对感受和情绪的领悟力来看,他自己就可以得到结论,除非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事情需要进一步澄清。事实上,第三次会谈时,卞医师显得很轻松愉快。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关于我的梦,梦境就像真实的会谈一样:他和我相对而坐,他正告诉我决定和太太离婚;可是逐渐的,我的脸从愉快的表情转成难过,而且变成薛先生的脸。这时他醒过来,发现自己在流泪。 这个梦的意义对他非常清楚:他的婚姻是对薛先生的回报,直到他遇到既了解又关心他的爱莉,使他想结束原有的婚姻。然而薛先生已经死了,他的罪恶感不是来自背叛太太,而是觉得背叛了她的父亲;他觉得自己违背了薛先生的托付。 病:如果我要离开太太,应该在薛先生还活着时这么做,那才算个男人。 治:可是那时爱莉还没有出现。 病: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我这么在意。以前遇到的多半顺其自然发展,有些会让我觉得兴奋,有些会说爱我,可是从来没有人让我这么爱自己。 但我在想你所说的“原谅”,我必须先原谅我自己,我想我做得到。刚刚可能让你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一结婚就有外遇,其实不是这样子。结婚前九年,我一直试图改善彼此的关系,希望不要虚度光阴。我曾告诉过你,我必须乞求她,她才和我亲热。整整九年,我每天都试着告诉她,如果我们努力去改善彼此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会完全改观;我们的婚姻虽然是别人一手安排的,并没有爱情做基础,但我们可以尽力去培养、改善彼此的关系。可是一个巴掌怎么拍得响呢?接着孩子出生了,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糟,我才开始打野食,弥补自己的需要。 治:你想自己为什么会在女儿出生后,去寻找外遇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病:我有想过。我本来期待小孩会使我们的生活不一样,我幻想所有的痛苦、失望、不愉快都会过去,结果却彻底失望了。我的小孩对我没有感情,她们拥有丰厚的信托基金,根本用不着像一般小孩一样依赖爸爸养活。她们出生的时候,我感受到很亲密的连结,高兴得彷若登天。我太太虽然不让我尽爸爸的义务,但是她的态度一点都不影响我对女儿的责任感,她们并非自愿诞生在这种畸型的家庭里。可是我没办法再忍受自己生活在这个感情沙漠里,我需要鱼水之欢以及伴随其中的感情。我不会自欺说这就是爱情,但我也不随便和人上床,也从未找过妓女,我外遇的对象至少是我对她有感情、而她也关心我的人。这种关系通常维持几个月,最长的一个来往了好几年。你甚至可以说我搞外遇是为了女儿的缘故,想藉此让自己的婚姻尽可能维持久一点。 治:如果薛先生还在世的话,你可能也藉此避免告诉他你想离婚。 病:你说得一点也没错。他那时还在世,直到十年前,他八十六岁的时候,才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过世。 治:所以你现在必须和自己的良心角力了。 病:上礼拜和你会谈后,我挣扎了很久。我很感谢薛先生,永远忘不了他,但我不想为此把自己的一生都赔上去。今天来看你之前,我已经决定,一定要离婚。现在我想到薛先生时,已不会有罪恶感,而我对太太的愤怒也已转成同情;她也是受害者,她一定像我一样,也希望能过不同的生活。至于小孩的部分,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许我自己能过得快乐一点的话,和她们的关系就会慢慢好转。 治:通常确实是这样。 病:我仍然希望薛先生能原谅我,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原谅自己了。 治:一旦弄清楚自己的症结在哪里,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病:我很谢谢你对我的帮助,真的帮助很大。(稍停)真令人惊讶…… 治:嗯? 病:我不曾想过要找别的心理医师,很自然就想到要打电话给你。 治:为什么? 病:大约五、六年前你在内科部开了一个研讨会。 治:对啊。 病:我也参加了…… 治:我记得。 病:我完全不记得那时上课的经验,可是现在突然想起来,你上课时说话的感觉,也可能是因为你总是穿三件式的西装,让我想到薛先生。你真的很像他。 治:所以你觉得可能会在我这里得到薛先生的谅解。 病:佛洛伊德真厉害,他真是了不起的人! 治:他确实是。 病:我应该读一些佛洛伊德的书。以前读过一些谈到他理论的书,但真要多知道一些的话,还是应该去读他本人的作品。 治:你说的没错,要了解佛洛伊德的理论就要读他自己写的书。 病:我可能会先读关于梦的书,或是一些导论性质的演讲纪录。 治:我建议你不要这样读,那些标题都是骗人的,那些书其实很难懂。你如果想直接去看佛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看法,可以读《外行人学精神分析的疑问》,这才是真正入门的文章。 病:好。谢谢你,更谢谢你帮我厘清问题,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再来找你。 治:没问题,祝你好运。 像卞新仁医师这一类型的病人,常在教科书上见到,但在临床实务中却不多见。他们借着正向移情关系的支持,把自己的心底事述说出来,从而自行导出解决困难的路,这时我的作用只在引导和肯定他。本来是依附环节的问题,结果借着自主性环节而成功解决了。通常案主如果能有所成长,并接受自己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是很重要的,焦虑就化解了。而且可预见的,像卞医师的情形,一旦他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时,对太太的愤怒就消退了,并代之以同理的了解。 卞医师所以能进步快速,是因为他没有受制于潜意识中的羞愧和罪恶感,而抗拒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会讨论到,这种抗拒会妨碍短期心理治疗的进行。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linzhangz.com/wljt/950.html
- 上一篇文章: 救命啊,谁来治一下我的妈妈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