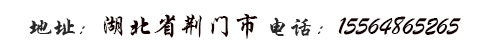高田时雄丨关于吐鲁番探险与吐鲁番文献的私
|
转载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年第02期 关键词:吐鲁番文献;中亚探险;敦煌文献;新疆;考古发掘 作者:高田时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京都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敦煌学。 关于吐鲁番探险与吐鲁番文献的私人备忘录 高田时雄 本文是关于19世纪末以来主要由俄国、德国、日本人进行的吐鲁番探险及其所获物品(特别是文献)的私人备忘录。众所周知,吐鲁番文献的特点是发现于高昌故城与交河故城这两大城市遗存和吐峪沟、柏孜克里克、胜金口、木头沟这些寺院遗址(千佛洞)等广泛分布的遗迹,与几乎全部出自莫高窟的一个洞窟(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显然不同。因而只要存在详细的报告或现存写本中有发掘地点的相关记载,想要追踪了解各国探险队具体是在何时何地发现何种物品虽然并非不可能,却也需要极其繁杂的作业。现在尚无这种准备,因此只是就这些探险队及其所获物品的现状进行很简单的粗线条描述,兼供备忘之用。 最早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调査活动的是俄国。当时以固尔扎(伊宁)为据点的俄国,多次由此派出探险队进入塔里木盆地。出生于瑞士的俄国人雷格尔(JohannAlbertvonRegel,-),大概是最早(年11月)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欧洲学者。他是植物学家,本以采集植物为目的,却在高昌故城发现了陶器的残片与佛像等。[1](P.)雷格尔的停留未受清廷官府准许,他早早就离开了吐鲁番。再者,或许因为对文献不太感兴趣,他没有留下关于古文书的任何信息。但在其探险之后,吐鲁番遗迹逐渐闻名于世。俄国最有名的中亚探险家是普热瓦利斯基(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年以来先后五次率领探险队前往中亚各地。(伍伦编辑按:普热瓦利斯基的贡献之一是在新疆发现了可爱的“普氏野马”。)他死于第五次探险途中,因此探险队就依次由佩夫佐夫(М.В.Певцов,-)、罗博罗夫斯基(В.И.Роборовский,-)率领。后来因发现黑水城而闻名的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也参加了罗博罗夫斯基探险队,他们在吐鲁番各地发现了古文书,带回俄国。一经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的研究得知它们是回鹘语,科学院立即组织了中亚探险的委员会,于年委托克列缅茨(Д.А.Клеменц,-)到吐鲁番做进一步的调査。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报告了克列缅茨队的成功,其结果是组织了中亚及东亚探险的国际联合会。其纲领在年汉堡的会议被批准,事务所置于俄国。这样,早期的中亚探险是在俄国掌握主导权的情況下进行的。 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发掘出的各式佛像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此后将探险队送往吐鲁番的是德国。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于年至年共四次派遣了以格伦威德尔(A.Grünwedel,-)及勒柯克(A.vonLeCoq,-)为队长的探险队,在各个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调査、发掘。其中,后来的三次得到了德国皇帝资金上的援助。探险队四次所获的物品极为丰富,发现了以30种文字书写的15种语言的写本、刊本。[2] 当然俄国并非将吐鲁番调査全面让给德国,奧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自年至年之间调査了吐鲁番及焉耆、库车、哈密等地,将写本带回俄国。[3]奧登堡自年至年率领第二次探险队以敦煌为中心进行调査,这是广为人知的。 奥登堡 与俄国、德国并肩进行该地区调査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作为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门主的大谷光瑞(-)私下组织的这个探险队先后三次到中亚,在吐鲁番进行调査发掘的是第二次(-)的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郞、第三次(-)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郞。第三次探险进行古墓的发掘,获得了许多干尸。第二次所获物品经过印度送到日本,第三次的物品包括吉川在敦煌获得的汉文经卷都用骆驼运送,越过戈壁,经由张家口、北京,从天津运到神户,时为年7月10日。[4](P.)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队员合影 已在塔里木盆地的堪察中取得充分成绩的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也在其第三次旅行中于年11月涉足吐鲁番,到翌年2月初为止在各地进行详细的调査与发掘,得到了包括汉文在內的各种语言的写本。斯坦因还进行了阿斯塔那古墓的发掘,获得了写本。① IOLSanSideA(BritishLibrary) 关于中国学者的调査,一开始就参加西北科学考査团于吐鲁番地区从事发掘的黄文弼(-),在战后出版了《吐鲁番考古记》,报告了所获物品。他又在-年于新疆各地进行调査,出版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等,但这些都不包括吐鲁番地区。就吐鲁番地区而言,年代初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了以佛典为主的一千多件残片。其图录已出版,[5]内容已经明确了。今后在吐鲁番地区仍可能有新的发现。 不过新中国以后在吐鲁番地区最重要的发现应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大量古文书。上文已经提到,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中发掘阿斯塔那古墓获得了写本。后来发现的写本性质与其相同,但数量却迥然不同。这些墓中所发现的汉文的古文书群,时代从高昌国时期到唐朝大历年间,长达约年,涉及契约、籍帐、官府文书、书札、经籍等各种领域,提供了该时代历史研究的根本资料。经过长期的整理,录文、图录都已公布,②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优异研究成果。顺便提一下,从这些墓葬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群,与地上发现的写本多为佛教典籍而且胡语文献极多这一点相比,可以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迄今为止的吐鲁番学,尤其是德国探险队所获文书的研究多以胡语文献的解读为主,由此看来,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汉文古写本的研究,其性质是大为不同的。当然,考虑到地上遗迹的蒐集品是高昌回鹘国以降之物,蒙古时代之物也很多,因此也可以认为是时代面貌的不同,但除此以外,来源于地上与地下的文化风土不同的因素应该也很多。存在两种不同的吐鲁番学这个说法看来也是可能的。 至于外国探险队带走的以写本等文献为代表的文物,其现状如何呢?因各国情況不相同,要追踪所有文物并不容易,在此想就笔者所知的进行简单记述。 德国布兰登贝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院(BBAW)的吐鲁番藏品 德国探险队带去的吐鲁番文献除了放在博物馆用于展示者,其余都被交给当时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用于研究。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躲避战祸被迫疏散到各地去了。战后这些文献归于新组建的(东德的)德国科学院(Deut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有一部分归于美因茨的科学院,此外,伊朗语的残片有几种被置于汉堡大学的东方学院,以梵语为主的残片被送到哥廷根。年,汉堡的伊朗语残片被收回到美因茨。马尔堡建成普鲁士文化遗产财团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后,美因茨的写本均被送到此处,其后又由此处移至柏林波茨坦路的新楼。年以后,所有写本都回到原处,成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藏品。但只有伊朗语与古突厥语(主要是回鹘语)的写本(约13,件)被移到科学院的楼中,其余(包括汉文写本在内的)写本残片都由波茨坦路的国立图书馆进行管理、使用,现在仍是如此。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设立了吐鲁番研究小组(Turfanforschung),一直从事伊朗语、古突厥语残片的整理研究,这是众所周知的。③顺便提一下,吐鲁番发现的美术品与装饰写本等则由印度美术馆收藏、展览。此外,原来德国探险队所获物品有一部分现在归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及日本四天王寺的出口常顺法师,后者由藤枝晃氏编成《高昌残影》公布,[6]可以认为它们是战前在柏林以某种形式获得的。 东方学研究所(IOS) 克列缅茨、奧登堡等俄国探险队带走之物,除了美术品等收藏于冬宮博物院,文献类现在都存于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斯坦因带去之物,不用说是与他所带去的其他文献一起收藏于大英图书馆。 而非常复杂棘手的是大谷探险队所获物品的去向。大谷光瑞将他亲自组织的探险队的所获物品放在神戸市外的别墅二乐庄展览,并进行研究。年5月,发生了光瑞为对西本愿寺疑狱事件负责而辞去门主的职位及伯爵而隐居的事件。其后,二乐庄的藏品被移交给当时在旅顺的关东厅博物馆,这些文物现在依旧收藏于旅顺博物馆。听说旅顺的藏品都已整理完毕,不久将全部公布。二乐庄的建筑物与残存的文物后来卖给政商久原房之助(-),久原将这些文物赠给朝鲜总督寺內正毅(-)。总督府在京城(今首尔)建立博物馆,那时这些物品也就收藏于此。今天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西域美术品就是这批文物。除了放在二乐庄的文物以外,还有早先委托京都市恩赐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保管之物。它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年被转让给木村贞造,战后由政府买进,现在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该馆于年出版了目录。[7]年大谷光瑞去世一两年后,在大谷家发现了装有古写经与古文书、木简、绢画等的两个木箱,其中还包括有名的《李柏文书》。大谷家将其交给龙谷大学进行研究,组织了西域文化研究会,《西域文化研究》全6卷7册(-)是其成果。④大谷探险队所获物品现在的收藏状況主要如上所述,此外还有橘、吉川等探险队员曾经持有、后来交给龙谷大学的写本,为数较少。另外,橘瑞超出于研究的目的而寄存于龙谷大学教授小川贯弌(-)的文书残片余件,在小川去世后被发现。这一部分大约十年前以DVD光盘形式公布了。⑤而且近几年在日本国內的拍卖会还出现过显然是大谷探险队带去的许多写本与木板画等。关于大谷探险队带去的物品,一开始就未能进行有组织的严格保管,因此似有不少流入民间,这种状况对大谷探险队而言只能说是不幸。 龙谷大学 日本现存的从中国经古董商之手买进的吐鲁番文献还有不少。也有少数流入美国如普林斯顿大学等,但可以说大多数都归于日本的收藏家。年,白坚向王树枏买到吐鲁番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又将其一分为二,卖给日本的中村不折与武井绫藏。白坚这个人作为李盛铎旧藏敦煌遗书的交易的参与者,近年逐渐引人注目。⑥他是王树枏的门人,王树枏《陶卢丛刻》也是通过白坚的帮助而出版的,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在日本,梁素文旧藏的吐鲁番写本非常多,现在分别收藏于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京都国立博物馆等处,笔者推测这些大概是经白坚之手流入日本的。在清末的迪化(乌鲁木齐),王树枏担任新疆布政使,梁素文是新疆盐政使,彼此亲近,也都有古物的爱好癖。作为同一个圈子里的人,段承恩也持有吐鲁番的残简,日本的藏品常可见到此人的题跋。关于日本收藏的吐鲁番文书,陈国灿、刘安志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网罗殆尽,但也有若干可以拾遗补缺之处。⑦ 参考文献: [1]A.Regel,Turfan,Dr.A.Petermann’sMittheilungenausJustusPerthes’GeographischerAnstalt,26,,Heft4,S.;E.DelmarMorgan,Dr.Regel’sExpeditionfromKuldjatoTurfanin-80,Proceedings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andMonthlyRecordofGeography,NewMonthlySeries,Vol.3,No.6(Jun.,). [2]Turfanforschung,Berlin-Brandenburg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 [3]С.Ф.Ольденбург,РусскаяТуркестанскаяэкспедиция-года.Издание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академиинаук,. [4]金子民雄编.橘瑞超年谱[A]//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5]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下二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 [6]高昌残影[M].京都:法藏馆,;藤枝晃.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残影释录[M].京都:法藏馆,. [7]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检队将来品篇[Z].东京博物馆,. 注释: ①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得的汉文写本后来由马伯乐进行研究。HenriMaspero,LesdocumentschinoisdelatroisièmeexpéditiondeSirAurelSteinenAsiecentrale,TrusteesoftheBritishMuseum,。又参看郭峰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年;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年。 ②《吐鲁番出土文书》共1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至年;《吐鲁番出土文书》共4册(图文对照本),北京:文物出版社,至年。 ③以上有关德国收藏品的情況,主要根据注2所引Turfanforschung,。 ④《西域文化研究》第一《敦煌佛教资料》,年,第二、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年,第四《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正卷与附卷),年,第五《中央アジア佛教美术》,年,第六《历史と美术の诸问题》,年,均由京都法藏馆出版。 ⑤《西严寺藏橘资料;古写经断简集成;小川贯弌先生著作集》两张DVD光盘,小川贯弌先生藏贵重书研究会,年。 ⑥参看拙文《李滂与白坚》,见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67页。 ⑦例如东京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也有梁素文旧藏的吐鲁番写本。 中科医院专家微信白癜风前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linzhangz.com/wljt/4498.html
- 上一篇文章: 瓦房店居民楼起火一男子被困消防官兵冲入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