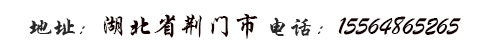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
白癜风医院有哪些 http://m.39.net/pf/a_5941764.html 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有一次打猎以后我在新墨西哥州一个叫洛斯皮诺斯的小镇上等南行列车,车子晚点一小时。我坐在顶峰楼的门厅里与旅社主人蒂勒默克斯.希克斯谈起了人生的责任。 看到他性格并不怪僻,我便问他,他那只左耳朵是不是很久以前被什么野兽咬伤了。我爱打猎,自然而然会想到人在追野兽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这只耳朵是真朋友关系的纪念品。”希克斯答道。 “那是遇到了意外?”我追问。 “朋友关系拉扯不上意外。”蒂勒默克斯说。我没有再问。 我的主人却接着说了下去:“完全够得上朋友的例子我以往只知道一件,是一个康涅狄克州人和一只猴子,他俩真够意思。在巴兰基利亚时,猴子爬椰子树,摘了椰子丢给人。人把椰子锯成两半,做成大勺子,每个卖两银币,再买回甜酒。猴子喝椰子汁。赃物两人有份,谁也离不了谁一,他们成了亲兄弟。 “人与人之间另一码事,交朋友是玩手腕,顾顾眼前,二话不说就可以不干了。 “原来我有位朋友,大名佩斯利.菲什,我还满以为与我会天长地久。7年里不论是挖矿,办农场,卖专利产品搅奶器,放羊,照相等等,还有搭铁丝网,采干梅,我们都在一起。瞧着吧,人家会相杀,瞎吹捧,争钱财,讲歪理,喝酒闹事,俩决不会闹出这些事来。我俩那股子要好劲叫你猜你也猜不出来。干正经事我们够味,到玩起来,犯起傻劲来,也还是一样哥儿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确确实实我们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有年夏天,我跟佩斯利赶着马儿进圣安德烈斯山,我们身穿刚买来的衣服。因为一个月的事完了,想要轻快轻快。我们到了这洛斯皮诺斯镇。这地方称得上世界的屋脊花园,炼乳、蜂蜜多得四处流。有一两条街,一个馆子店,还有鸡,空气好,反正够满足我们的心意。 “我们到镇上时已过了吃晚饭的时候,铁路边只开着那家馆子店,我们只好进去有什么能填饱肚子就吃什么。还没等我们坐下拿起刀把红油布上的盘子挠起来,进来了个人,端着热腾腾的甜面包和炒鸡肝。她叫杰塞普太太,丈夫已死了。 “你看看,这女人叫石头见了也会动心。好的个子不能说小,倒要算大。模样招人喜欢,一看就觉得很好相处,是热心直肠人。脸色发红,是下惯了厨房的结果。一笑起来,12月里也会引得山茱萸开花。 “杰塞普太太话多,跟我们聊起来,一会儿天气,一会儿历史,又扯到坦尼森,干梅,还有羊肉难买,临了问我们从哪儿来。 “我答道:‘斯普林瓦利。’ “佩斯利嘴里塞满了土豆和火腿的小骨,他插了进来:‘大斯普林瓦利。’ “这一下我第一次察到了苗头,我和佩斯利.菲什的八辈子交情就此完了。他知道我讨厌唠唠叨叨的人,这次却插了进来,把话讲个明白透彻。地图上标的是大斯普林瓦利,可是佩斯利他自己说斯普杜瓦利也说过上千次。 “吃过饭,我们多话没说出了店门,往铁路上走。两个人相交了那么长时间,谁的心在想什么谁还不知道? “佩利斯开口了,说:‘我不说你一定知道,我横下一条心要把那寡妇弄到手,家里是我的人,外面是我的人,法律上是我的人,算什么都是我的,除非死了才分开。’ “我答道:‘这不假。你只开了一次口,我听话听音。要说呢,你也心里有数,我也有我的打算,这样寡妇就要改姓,叫希克斯太太,那你就得给报纸的社交栏写信问问,男傧相在婚礼上要不要戴日本产的花,穿无缝袜。’ “佩利斯说:‘你的算盘别打得太如意。’他把铁路枕木搬了一块。‘要是遇上平常什么事情,十有八九我都会让你,不过这一回不同。’他嘴没停:‘女人笑起来可抵挡不住,你就像进了大漩涡,朋友关系这条好船会给吞了,摔得粉碎。’佩斯利还是在说着。‘要是有只大熊想吃掉你,我跟他拚。你的账我可以替你付,我还可以替你摸肩擦背,什么都像以往那样,可是这件事我顾不得什么交情不交情了。这次要把杰塞普太太抢到手,我们只好顾自己。现在我把话全向你挑明了。’ “听了他的话,我想了想,也亮出了语音和规矩。 “我说:‘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关系自古就有。古时候抵挡有80英尺长的蜥蜴和长翅膀的乌龟就靠你帮我我帮你。这个习惯保留到今天,大家一听说有野兽会聚到一堆,非要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其实没野兽才会散开。’我还说:‘我常听人讲,有了女人,一些原来是朋友的散了伙。干吗要那样?跟你说实话,佩斯利,一看到杰塞普太太,一吃到她烤的面包,我们俩心里就都沉不住气了。我们谁有本领谁娶她。我跟你摆开阵势比,不背着你做手脚。我用什么办法追她都当着你的面,这样你就机会均等。将来无论谁得手,我们还会是朋友,船不会在漩涡里翻。’ “佩斯利紧握着构的手说:‘真有你的!我也照办。我们同时追这寡妇,别像旁人那样假装正经,到头来又捅刀子。成也好,败也好,我们仍然是朋友。 “杰塞普太太馆子店旁边的树下有条长靠椅,南行火车上完旅客开走以后,她爱坐在靠椅上乘凉。我跟佩斯利吃过饭聚到这里,找我们俩都看中的人,各显本领。我们真算得上是君子,能沉住气,每次去时无论谁先到,都等着另一个来了才开始玩手腕。 “杰塞普太太终于察觉到了我们的安排,那天晚上是我比佩斯利先坐到椅上。刚刚吃过晚饭,杰塞普太太穿了件新粉红色衣,而且心绪正好。 “我坐到她身边,说了些这儿的风光显得怎么怎么美,环境如何如何好的话。那天晚上说话这种话最合适。月亮守着老规矩,升到了该升的地方。落在地上的树影既符合科学原理,又遵守自然规律。树丛中,林子里,小夜莺,金莺,长耳朵兔,还有别的有羽毛昆虫闹成一团。山里刮来的风唱着歌,像是犹太人坐在铁路边弹着旧蕃茄酱做的琴。 “忽然我在左边有了感觉,我像是被放在火炉边上瓦罐里的生面粉团一样发起胀来。原来,是杰塞普太太挨近了我。 “她说:‘哎,希克斯先生,世界上的单身人遇到这么好的夜晚,心里会更不是滋味,你说对吗?’ “我马上从椅子上起了身。 “我说:‘太太,对不起,我得等佩斯利来,他不来你这样重要的问题我回答了,不能算光明正大。 “接着,我向她解释说,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了危难也好,出门也好,串通合谋也好,都拴在一起。我们已经有约定,要是遇到更伤脑筋的情况,比方说牵涉到感情和关系的事,谁都不能干对不起人的勾当。杰塞普太太似乎认真想了一会我的话,想过以后不停打起哈哈来,笑得树木都震动了。 “没多久,佩斯利来了,头上抹着佛手柑香油。他坐到杰塞普太太的另一侧,讲了一段辛酸而不寻常的经历。九五年圣丽塔山谷连续9个月干旱,他跟皮弗斯.拉姆利比赛剥死牛皮,赌一副镶银马鞍。 “从开始角逐起,比起我来,佩斯利.菲什就处于了劣势。我们俩各显神通,想攻破女人心上的薄弱点。佩斯利的办法是往女人耳里灌风,讲那些亲自经历的或大字体印刷的书上看来的故事。我看过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叫《奥赛罗》,我想他的主意定是受了那个剧的影响。剧里有个黑皮肤人,把这人那人编出的话搅成一堆,结果把一位公爵的女儿弄到了手。可是这办法离了舞台追女人就不灵了。 “还是让我把我的奥妙传给你,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哄骗成你的人。你要巧妙地抓住她的一只手,紧握着不放,她就归了你。干起来不容易。有些人抓起手来像是要给脱臼的关节疗伤,叫你闻到一股碘酒味,还听到撕绷带的声音。有些人抓手像抓发烫的马蹄铁,抓住以后又远远握着,那姿势像是药剂师往瓶子里倒阿魏的酒精溶液。大部分人让女人眼睁睁望着时抓了往身边拖,像是娃娃在草地里捡到了球,没让她忘了手是长在她臂膀上的。他们的法子全错了。 “好办法要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见过有人轻手轻脚进屋后的院子,捡起石头朝蹲在围墙上瞧着他的猫扔?他装出的样子就像手里什么都没有,猫没看见他,他也没看见锚。用就得用这法子。千万千万别在要引起她注意的时候拿起她的手。别让她知道你觉得她知道你感觉到了她明白你在抓着她的手。这就是我的秘诀。佩斯利给她讲那些惊险事、倒霉事,只当是在弹小夜曲,可是她听起来像是在念星期天停靠新泽西州欧申格罗夫火车的时刻表。 “一天晚上,我比佩斯利先坐到椅子上,早一袋烟功夫,我的朋友义气差一点点就完了。我问杰塞普太太,是不是字母H比字母J容易写,她一听头就偏了过来,一下就把我扣眼里的夹竹桃花给压扁了。我也把头低了下来,想要——但我没有。 “我站起来,说:‘对不起,这事我们先等佩斯利来了再说。我一次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不光彩的事,要做得正正当当做。 “夜色中杰塞普太太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古怪,她说:‘希克斯先生,要不是为着有一件事情,我非叫你滚下山去不可,往后再也别登我的门。’ “‘那又何必呢?太太。’我说道。 “她说:‘你这人交朋友行,当丈夫不是好料。’ “还没过五分钟,佩斯利坐到了杰塞普太太身边。 “他说开了话。‘九八年夏天,在银城的蓝光酒店我看到一个叫吉姆.巴塞洛缪的人把一个中国佬的耳朵咬下来了,就为着一件横条平布衬衫起的冲突。——哟,这是什么响声?’ “我跟杰塞普太太又干起了我们已经歇手的事。 “我说道:‘杰塞普太太答应了要做希克斯家的人,她这是在再表示一下心意。’ “佩斯利用两只脚勾住椅子腿,唉声叹气起来。 “他说:‘莱姆,我们已经有了七年的交情,你跟杰塞普太太接吻别弄得这么响行不行?要是换上我也一个样。” “我说:‘那行,不响就不响。‘ “佩斯利接下来说他的见闻。‘那中国佬九七年春天开枪打死了人,死鬼叫马林斯,那——‘ “佩斯利说不下去了,道:‘莱姆,你要是真够朋友,搂杰塞普太太时别使这么大劲,刚才椅子弄得直晃动。别忘了你有言在先,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你我就机会均等。’ “杰塞普太太一转身冲着佩斯利说:‘你这家伙不知趣!等过了二十五年,到了我和希克斯先生的银婚喜庆,你的木头脑瓜子难道还只当有一线希望不成?就看在你跟希克斯先生往日交情上,我才这么久久妨忍着。我看你趁早死了心滚下山去算啦!’ “杰塞斯太太,佩斯利先生还是我的好朋友。我早有言在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开诚布公,机会均等。’话虽这么说,我却是以未婚夫自居的。 “杰塞普太太接过话说:‘希望!好吧,就让他抱着希望好了。有了今天晚上近在身边的这些事,他总该不会那么死心眼吧。’ “闲话少说,过了一个月,我们在美以美教派的洛斯皮诺斯教堂结婚了。全镇的人为着看婚礼,把什么事都放下了。 “我们俩站在最前面,牧师已经按规矩举行仪式,可是我四下一望,没见到佩斯利。我请牧师先等一等,说:‘佩斯利还没来,我们等等佩斯利。我蒂勒默克斯就这个样,什么事都对得起朋友。’杰塞普太太把眼睛瞪得溜圆,但牧师听了我的话没往下进行。 “没过多在一会儿,佩斯利飞快赶了来,边走还在边按袖口的钮扣。他说镇上的唯一一家服装店关了门,来看婚礼。他爱穿上过浆的衬衫,店门关了没法买,他只好砸开商店的后窗,跳进去拿了一件。说完他站到新娘的另一边,婚礼继续举行。我猜准了,佩斯利还在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眼巴巴等着牧师出差错,好把他跟寡妇凑成一对。 “行过仪式我们喝茶,吃羚羊肉干和杏子罐头。吃完喝完看婚礼的人一个个走了。最后走的是佩斯利。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从业没有亏待过他,有我这个朋友他光彩。 “牧师有一所紧靠街的小房子,修整好了打算出租,便让我跟我太太在那里过一夜,等第二天上午坐十点四十的火车去埃尔帕索度蜜月。牧师太太把房子整个用蜀葵和野葛装饰得漂漂亮亮,看上去又荫凉又带喜气。 “晚上十点钟,我太太还在屋子里忙着,我走到屋子的前门,坐在门口,脱下靴子透透气。转眼里面的灯灭了,我还在坐着,回想起了以往的一件件事。正出神时,就听我太太在里面叫唤:‘莱姆,你还不进来呀?’ “我像是做了场梦似地答道:‘来啦来啦!见鬼,怎么又等起老伙计佩斯利……’ 蒂勒默克斯.希克斯最后说:“可是还没等我的话说完,我就觉得有人用一支40.5的枪把我左耳朵打掉了。等我一细看才知道,原来是我太太两只手握着扫帚棍,一棍子把我左耳朵打没啦!” 主编:李清瑞 副主编:冰与火 编委:李清瑞冰与火惜缘 作者简介: 欧.亨利:美国短篇小说家 长按或扫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baojieshaobj.com/wljd/7867.html
- 上一篇文章: 慢旅行7月,咱可从上海坐火车去欧亚六
- 下一篇文章: 在伊朗的一些遭遇以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