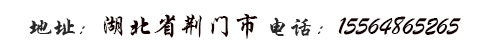爱丁堡雨中来客
|
按我原本的习惯,游记总是要在目的地完成,因为被陌生的景色和人群所激荡的心境稍纵即逝,如果不及时抓住,就要在日复一日的睡梦中消散去了。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展示着,那些你习得的知识,一个小时后会忘记一半,六天后就只剩下四分之一,旅行里产生的心绪也是如此——也许会比那些知识遗忘的慢一些吧,可却又不能像它们一样,被常常复习。一旦离开那个特定的地方,回味的感悟就变成一件飘渺而矫情的事情。而这一次记叙的过程几乎算得上旷日持久,究其原因,就要追寻到我那场被爽约的湖区之行去了,此处按下不表。无论如何,当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距离我第一次踏上爱丁堡的土地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但就像艾宾浩斯曲线里永远不会被遗忘的百分之二十一样,我和爱丁堡之间的故事,总有那么一部分被记忆的潮汐淘洗出来,在独属于我一人的海滩上熠熠生辉。从曼彻斯特去往爱丁堡的火车在公寓附近的小站OxfordRoad出发。从蜿蜒的阶梯上去,经过地铁闸机般的检票口,就看得到细瘦而漫长的铁轨,从英格兰的脚下一路蔓延到对苏格兰的幻想里去。 OxfordRoad火车站入口 英国的火车与国内不同,三分之二的车票固定了座位,剩下三分之一就像公交车一般,全凭运气,先到先得。如果坐满了,就要到两节车厢当中去,那里靠窗有一排可以坐的地方。我和Abigale的车票恰好就是那三分之一,我们靠在车厢壁上聊天,开玩笑说应该是天气太好的缘故,阳光灿烂,因此连车厢连接处的临时座椅上都长满了英国人。火车晃了一个小时,到了兰开斯特,我们才终于从一对留学生手里接管了两个座位,而困意也很快从脚跟攀爬上来,接管兴奋的大脑。我们几乎一觉睡到了目的地。在旅行计划中,我们要先去苏格兰国立博物馆,再去看王子街花园,然后趁着夜色还未降临,找到位于新城区的居所。但当我们离开威瓦利火车站的穹顶,第一眼见到爱丁堡时,我就知道我的计划将要遭遇巨大的挑战——当你身边皆是可爱风景,你很难硬下心肠目不斜视地前行。王子街花园和老城 星期天的王子街热闹而拥挤,人行道被公交车站占去一半,又被坐在花坛边男男女女指尖的星火和烟雾占去另一半,仅留下一条缝隙共行人穿过。我们抱着背包和被长途火车晃出的疲倦向白雾中那条通道走过去,白雾却在同时后退,一直退到远处司各特纪念塔高耸的塔尖背后,成为天幕上一团软绵绵的云朵。游人好奇的视线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追随云的影子在天空中溯源而上,向上,忽然就再见不到云了。岭云散尽楚天高,你到了想象的最顶峰,终于力竭,脱了力般向下坠落,就如白日里无声的闪电,天然要被这块小小的旷野中最高的金属塔尖引诱,再向下,终于停驻在中空的黑塔里坐着的瓦尔特·司各特雕像上。于是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庆幸大理石凿出的雕像在此刻竟变得足够柔软,柔软到能接纳一双从九天跌落的眼睛。我在塔边售票亭外的人物介绍上,做与这位“欧洲历史小说之父”仓促会面之前的临时抱佛脚。但当我鼓起勇气去凝视这座大理石塑像时,他下垂的眼尾只是忧伤又平静地投向一处未知的落点。ScottMonument司各特纪念碑 沿着司各特雕像脚下的草坪一路向前,在国家美术馆的前面有一个街头乐队正在演出,主角是传统的苏格兰风笛,配乐却是架子鼓和电吉他。吹风笛的男人穿了一条棕绿色的苏格兰裙,欢快的旋律令过往的行人不禁驻足。遇见大象咖啡馆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个原本普通的咖啡馆因为孕育出了J.K.罗琳笔下那个光怪陆离又引人入胜的魔法世界而声名鹊起,我们沿着山路向下,原本是奔向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却在这里注意到了店里塞得满满的顾客。退后一步,才看到红底金字的店名“theelephanthouse(大象咖啡馆)”,和玻璃上的一行字:“BirthplaceofHarryPotter(哈利波特的诞生地)”。有趣的是,在这行字下面还有一行中文,写着“魔法咖啡馆”,可见应当有太多中国人慕名来这里打卡。店里人很多,挤得像圣诞节时霍格莫德的蜂蜜公爵糖果店。游人如织的大象咖啡馆 我们没有进去尝尝那杯能使人灵感迸发的咖啡,终于赶在闭馆前拜访了苏格兰国立博物馆。博物馆一层展厅里有座建造于年的“千年钟楼”,高十余米,分为地窖、殿堂、钟楼和尖塔四个部分。最下层的地窖里,一只斑斓的埃及猴子正转动着驱使整座时钟运转的齿轮,齿轮上蹲立着一尊未名的古神。第二层的殿堂上散落着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略显扭曲的形象,代表着欧洲人对二十世纪最糟糕的记忆,而卓别林和其他动画人物组成的游乐场,却将上个世纪的快乐凝练成一个个可爱的具象。在一切欢欣与痛苦的交织中,嶙峋的骷髅死死抓着细杆由上而下,细杆的尽头连接着一面镜子。你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第三层的钟楼没有刻度,一个由12个人物组成的圆圈缓慢转动着,每个雕像代表一个月份,也代表一种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时间在这里被无限缩短——转完一圈便是一年;却又被无限拉长——饥荒、战争、迫害所带来的痛苦被永久定格在雕像的脸上。比起下面三层,塔尖显得寂寞许多。一个女性的形象孤独地站在那里,怀着抱着一位逝者,这就是Pietà,意大利语,意味同情与怜悯。如同一切颜色的总和是黑,设计者认为,Pietà是人们怀念过去时产生的一切情绪的总和,也是我们前进所需要的一切力量的来源。千年钟楼的斜对面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昆虫标本,达尔文的隔壁是奈皮尔的对数和公鸡,我看不懂这个展厅布置的逻辑,但这似乎产生了奇妙的反应。时间在这里被简单的区分为过去和未来,卒于年的数学家一定没想过自己能和两百年后的一位享誉世界的生物学家做邻居。可两百年的时间在博物馆的比例尺里,只是两个相距数米的展柜而已。另一件值得记述的藏品是40英尺长的鲸鱼头骨。这是一条上世纪末搁浅在福斯河河滩的抹香鲸,它的名字叫做莫比。人们在福斯河里发现它后,曾拼命想让它回到海里,可惜最终他们并未成功。莫比死后,它的骨架被运到博物馆里,连同这段故事一起被妥善保管起来。走出博物馆时,爱丁堡下起了雨。大雨让整座城市笼罩在湿润的雾气里。我们的住处在新城一位老妇人的家里。从王子街向东翻过一座起伏平缓的山,紧接着就是一路下山,越走越开阔。你能看到遥远的海岸,在那一刻仿佛近在咫尺。老妇人热情地迎接我们,她养了一条狗,按年龄来算也该是位老太太了。它绕着我的被雨水打湿的裤腿晃着尾巴转圈。我收起雨伞,忍不住向老妇人抱怨下雨的不便,她笑眯眯地说:“大雨是贵客,你们也是。”从城堡上俯瞰爱丁堡 第二天,我们在大雨中拜访了爱丁堡城堡。雨水和寒意都落进怀里,打湿了我决意留作纪念的门票。城堡有多年的历史,玛格丽特王后于年在此去世,她的儿子大卫一世在这儿为她建造的小教堂是爱丁堡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独立战争期间,这座战略要塞的归属几经周折,最终在年回到了苏格兰人手中。城楼上一排乌黑的炮筒还留着几分当年的硝烟,天色沉沉,魂魄来聚,埋着玛格丽特王后骨骸的土地上埋着战士的尸骨,无贵无贱,同为枯骨。但此刻,战争的残酷与血腥都在消解游人细碎的感慨中,变成每天下午一点的那声报时的炮响。从城堡出来,左手边一排卖羊毛围巾的店铺,摆满了各种花色的格子,右手边是苏格兰威士忌中心。碍于路途遥远,带着一瓶酒多有不便,我最后买了两块酒心蛋糕当作纪念。第三天我们计划去攀卡尔顿山。可上山的路空无一人,大雨瓢泼,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最后放弃了在山顶一瞰爱丁堡的计划,只在标示牌前合影,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回程的路上,我们还遇到了《速度与激情9》的拍摄组,可惜没有亲眼见到范·迪塞尔,只能一瞥好莱坞现代电影工业的倩影。卡尔顿山和《速度与激情9》拍摄用车 大雨一直未停,我们从皇家大道上的一条小路向下,走一条蜿蜒的楼梯,路过爱丁堡大学的某个学院,就回到了王子街上、回到司各特的大理石像面前。所有人都撑着雨伞,我的视线被层层叠叠地遮盖,但我仍能从记忆里找寻到一块粗略的地图,那是我用脚步与目光亲自丈量出来的——从这里向东是新城,向西是老城。爱丁堡大学爱丁堡是山的城,尽管未上卡尔顿山,亦未能一登荷里路德公园的亚瑟王宝座,但我们这三天的旅行却无时无刻不在山上。这里的山不是举手可近月的太白峰,没有一径入云斜,也不住着卢处士(新城里倒是住着许多画家和他们的画),只有漫长的起伏。假若你第一眼见不到山,那步行时大腿上传来的酸楚也一定做个及时的提醒。背着行李回到曼城,离开不过三日,竟有种阔别的体会,这个只待了数月的地方已让我有了种熟悉感。在漫长又香甜的一梦后,我鬼使神差地打开手机去查询爱丁堡的天气。晴朗无云。我忽然想起老妇人的那句话,大雨是来客,我们也是。特别鸣谢:此次同行的Abigale 林白鹊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baojieshaobj.com/wldy/5615.html
- 上一篇文章: 瓦努阿图移民的真相是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